| 首 页>陋室斋>应天常教授论电视文化>寂寞悲壮的执着与坚守——评纪录片《风雪可可西里》 | | 您好!今天是: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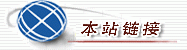 |
||
|
|
||
本站其它链接 |
||
搜索本站更多内容 |
||
——评纪录片《风雪可可西里》 作者:应天常 |
作者:应天常 来源:研讨会书面发言 本站编辑发布 |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新疆克拉玛依工作过几年,偶见沙漠边缘跳跃着倏忽即逝的藏羚羊十分好奇。当地人告诉我,成群的藏羚羊在可可西里。我知道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可可西里在藏语中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的意思,是中国最后的原始荒原,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有人说“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但我一直没有去,因为我后来听说那里盗猎十分严重,新疆石油工人利用藏羚羊趋光的习性,深夜里开卡车打开光亮的车灯向着惊慌奔突而来的高原精灵冲过去,然后笑着唱着满载“自投罗网”的藏羚羊回来,烹煮血肉模糊的羚羊肉做下酒的佳肴。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新疆克拉玛依工作过几年,偶见沙漠边缘跳跃着倏忽即逝的藏羚羊十分好奇。当地人告诉我,成群的藏羚羊在可可西里。我知道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可可西里在藏语中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的意思,是中国最后的原始荒原,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有人说“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但我一直没有去,因为我后来听说那里盗猎十分严重,新疆石油工人利用藏羚羊趋光的习性,深夜里开卡车打开光亮的车灯向着惊慌奔突而来的高原精灵冲过去,然后笑着唱着满载“自投罗网”的藏羚羊回来,烹煮血肉模糊的羚羊肉做下酒的佳肴。
践踏着盗猎者的脚印的可可西里,不是我向往的旅游胜地。
从此,我隐忍着对藏羚羊命运的忧虑,关注着可可西里。在陆川的《可可西里》、在四川电视台彭辉的《平衡》、央视陈小元的作品以及刘宇军的《风雪可可西里》里,我没有见到石油工人狡黠直接屠戮藏羚羊的镜头,但是,我看到了他们作品呈现出来的各不相同的“可可西里”。
陆川的《可可西里》国际获奖,但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残酷的杀戮和死亡。从触目惊心的天葬到盗猎者剥杀藏羚羊的皮、成群的秃鹫盘旋啄食一块块血肉和尸骨。盗猎者的报复屡屡得手,枪杀了巡山队员强巴、巡山队员咬牙枪杀剥羊皮的20岁少年马锐,接着是巡山队追捕逃跑的马占林父子,这对父子终因陷入严重缺氧状态突然倒地,仰面苍天口吐鲜血痛苦死去。接着,是巡山队员刘栋之死,陆川着力刻画刘栋面对死亡来临时的悲苦挣扎。影片的结尾更加残酷,狡诈阴冷的盗猎分子砰然开枪,杀死了野牦牛队队长日泰……
诚然,血色的恐怖充盈着可可西里,但我觉得压抑;频繁剪切与多角度的拍摄可以产生视觉的冲击力,“构成”一部故事性很强的影片,但是,纪录片的本质是还原生活,面对这样可怖的、令人窒息的、密集的“真实”,我看到可能是陆川眼里的“可可西里”,又有些疑惑——影片是否真的还原了可可西里,还仅仅还原了作者想象的可可西里,或者说呈现了满足观众窥视期待的可可西里?
现实中的可可西里,是海拔4700米的高原,自然环境恶劣,气候寒冷,每天不是风雪交加,就是流沙漫天。世代繁衍生息于此的藏羚羊由于不法分子的恣意猎杀,由原来的100万只猛然降至不足1万只。当地人为保护藏羚羊不至于灭绝,“擅自”于1993年成立由藏人日泰等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巡山队”——这就是陆川《可可西里》的选材。
与此相比,刘宇军的《风雪可可西里》让我看到了更实在、更真诚的可可西里。这个纪录片谈不上独特的构思,也没有什么新颖的表现手法,但我欣赏刘导演收敛而不煽情的“呈现主义”处理方式。虽然“呈现主义”难以把握,需要控制,但他仍然坚持采用一种纯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原生状态下的人。美国的大卫•梅朵在《导演功课》中说过:“艺术家的任务是把最简单的技术用得完美,而不是去学太多的技术。如此才可以使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容易的事变成习惯,习惯的事因此可以变得更加美妙。”
就这点来说,刘宇军先生是一位诚实而有自知之明的导演。
优秀的纪录片都热衷于讲述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把文学叙事技巧借鉴到纪录片的制作中来,叙事对象更加个体化,叙事本身更讲究情节化,注重悬念和高潮的设置,以开放式叙事结构的安排处理题材。在《风雪可可西里》,刘宇军不紧不慢地讲述了野牦牛队一次巡山的过程,以此为主线,从格尔木向北至新疆,再南行穿越昆仑山到达青海、西藏、新疆的交汇处,这是藏羚羊南迁的必经之地。故事在6万平方公里、海拔5000米的广袤的青藏高原展开。他们艰难跋涉,过河,车坏了;吃饭,满嘴沙子;在车子里睡觉……节奏似乎有些放纵,却也起伏跌宕——突然在“沙娃宾馆”发现敌情:盗猎者抢先进入无人区,然后野牦牛队开始了艰苦的沙漠追寻、追捕。镜头语言酣畅地揭露了盗猎者疯狂和残忍,也真实记录了盗猎者被捕后的惶恐和狡猾,潜逃后被捉的胆怯和无奈。作品充分体现创作者视纪录片真实性为第一要素的职业理念,值得称道。 (未完,接下页)
| (本站2011年8月2日发布) |
|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
| 上一篇:应天常撰文-《马后炮·序言》:新闻都是马后炮 |
| 下一篇:应天常教授:“官方舆论场”质疑——兼与人民网总裁廖玒先生、复旦大学教授童兵商榷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原名【语文·教育·研究】)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7.0以上版本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联系本站 E-mail:yxj701@163.com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