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反右专辑>章立凡:章乃器在1957年(转载) P.3.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历史人物】 |
 |
| 作者:章立凡(章乃器先生之子) |
| 作者:章立凡 来源:维普资讯/浴火凤凰网 本站编辑转载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五
6月8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有批判者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领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的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解,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辩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六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
他在6月10日工商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
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评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老,你是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明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七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前面提到的民建那位老先生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份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公的良苦用心,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二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能自辱其祖的。这段报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报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上,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
“……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八
父亲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
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
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6月19日,这篇讲话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位当场聆听过讲话的“大右派”,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6月25日这天,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
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混战,秩序纷乱。父亲力持已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像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公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20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父亲专门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这两年周公处境不好,被迫做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
父亲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作了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父亲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一些老前辈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此事。
接下去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
例如当时各报都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回忆一件往事兼质问章乃器》一文,大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际,是他所在的游击队将章乃器、胡风、史良、邹韬奋等人救出,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战士谴责章乃器:“在最艰苦的时候,党派了自己的儿女用生命搭救了他,解放后又把他放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而章竞“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最后他用“这种人简直没有人味!”的粗话,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义愤。
——事实上,香港沦陷时,章、史二人都在重庆。这位老战士可能是记忆有误,但历史岂是能够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 ;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
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
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点击右图返回: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 “整风-反右”历史记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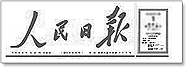 |
|
【延伸阅读】
|
|
| (2003年7月11日编辑转载 / 2018-12-03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