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沉重的1957-1965>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历史纪实)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近 期 评 论 |
点击:更多评论
| · “反右运动”纪录与反思 · |
|
| 作者:戴晴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2003年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
【本站按】 储安平,解放前为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多年担任教授、编辑,主编《观察》等进步刊物,针砭国民党当局时弊入木三分。至今仍可读到的《一场烂污》即是一例。 1949年到北平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 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同年中共“整风”期间,响应“鸣放”号召,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反右中被称为“党天下”的著名言论),1958 年1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文革”再遭残酷迫害,后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间蒸发,时年57 岁…… 储安平的“右派”至今未获“改正”。戴晴著《储安平与“党天下”》1988 年正式出版。 |
| 点击标题浏览: |
1、帽 子 |
2、社会主义阵营 |
3、个人英雄主义 |
4、勉 强 |
5、谋 |
6、命 |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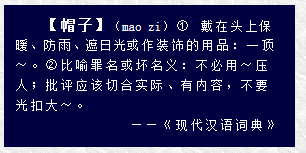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 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 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 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
▲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 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 年5月8日,55 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 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
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到了1980 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的,只剩下10 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 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 5 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 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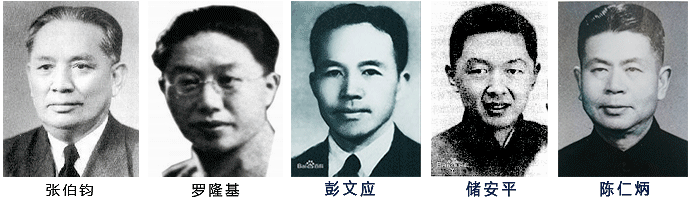 |
他们当中,19 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 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 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19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胡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1969 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
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又被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 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可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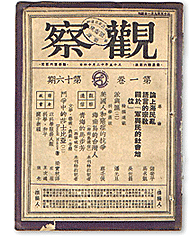 对于统治了中国20 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对于统治了中国20 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点击浏览);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点击浏览)。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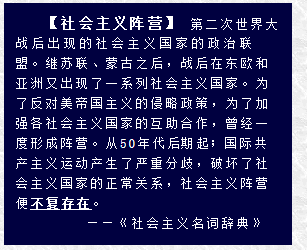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囫囵个的“阵营”如何出现一条条裂痕,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1948年被开除出9 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1956 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20 次代表大会和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
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① 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 7 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点击看短视频)
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目前,对此种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 年之后——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 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施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 1950年5月 |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
| 10月 | 镇压反革命 |
| 1951年5月 |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
| 11月 |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
| 12月 | “三反”运动: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
| 1952年1月 | “五反”运动: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
| 1954年2月 |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
| 10月 |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 《文艺报》 |
| 12月 | 批判胡适思想 |
| 1955年2月 |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点击:案件始末) |
| 下半年 |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反”) |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鲧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他是抖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其肉身早已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扣了金钟、上了紧箍或吓破了胆。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当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
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帖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训斥辱骂提反对意见的人”的白司长冲突起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并发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气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于是出笼。标志王蒙创作水准的,当然是1986 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了。但如果我们回到1950 年代,将这位作者的开笔之作《小豆子》与1956 年那篇受到来自相当一级的压力与批评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出,逐渐成熟、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切切之情的文学家们,正要冲破那只有纯朴的蒙昧才感到自在的一味歌颂的樊篱,向着直面生活并且热烈地干预生活转化。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闻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1956 年,记者们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这种文字今天是极难见报了。对黑龙江森林大火的报道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本站补注】 所谓“左叶事件”:1957 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刘少奇的陪同下参观农业展览馆,由时任农业部部长助理的左叶担任向导,并负责维持秩序。由于去的人较多,放进去的记者也多,因此在采访的摄影时发生了拥挤,左叶由于重任在身,变得急躁起来,恰在此事中国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拉了他一把,要他闪开点以便拍照,双方于是发生了争执,左叶出言不逊,引起各报记者反感。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场参加摄影采访的记者洪克写了题为《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小品文,不点名的批评了左叶。《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的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恼》,报道了这个事件,同时还专门配发了社论 《尊重新闻工作者》。后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的诗,并配发了讽刺漫画。其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同年5月11日,新华社又发了通稿,使这件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
但是,反右斗争开始后,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新闻工作者获得平反。这一事件对此后的新闻摄影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出的话语: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出的话语:
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②。这种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他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像后来的雷锋、像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加上他本人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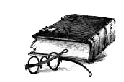 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② 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棐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延伸阅读】 |
||
|
||
| (本站2004年6月8日编辑转发/ 2022-04-07 更新) | ||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站长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