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教育理论>教育随笔>应学俊:中国教育改革,敢问路在何方?——关于中国教育改革断想 | | 您好!今天是: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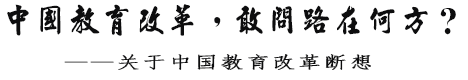 |
| 原创撰稿:应学俊 本站 2010年3月18日编撰发布 (2016年6月修订/更新) (本页浏览:人次) |
名曰“断想”,那是因为题目太大,想不周全,也没那个水平;但毕竟干了一辈子教育,也做过一些研究和思考,所以还是有些心得和研究结果,记录下来,名曰“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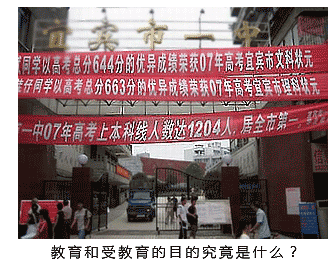 目前,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许多问题已经有所考虑,在很多方面规划还是不错;但对某些问题甚至是根本问题有时又使人感到似乎有所疏忽或是回避?有的方面也无法排除有认识误区,总觉得某些方面有些隔靴搔痒,恐难奏效。既然征求意见,鼓励讨论,那就写下来吧。面对中国教育的许多“乱象”、“病态”,有时真还有些着急,如此下去教育将会怎样?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怎样?
目前,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许多问题已经有所考虑,在很多方面规划还是不错;但对某些问题甚至是根本问题有时又使人感到似乎有所疏忽或是回避?有的方面也无法排除有认识误区,总觉得某些方面有些隔靴搔痒,恐难奏效。既然征求意见,鼓励讨论,那就写下来吧。面对中国教育的许多“乱象”、“病态”,有时真还有些着急,如此下去教育将会怎样?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怎样?
若论“教育改革”,中国教育可谓一直在“教改”之中——从毛泽东时代直到当今,但也一直在遭诟病之中。那么,中国教育改革,出路究竟在哪里?
● 任何改革都必须老老实实遵循客观规律
“改革”就是要把事情办得更好更对;“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但是,有时人们重视这个重视那个、把握这个大局那个原则,唯独忘了不可违反的客观规律。其实“科学发展观”要义之一也就是不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毛泽东的“教改”搞不成功,并非毛的教育思想一无是处(有的至今也还有借鉴价值),但毛的“教改”因极左乌托邦而走火入魔,留下“凭手上的老茧上大学”一类历史笑柄;其实就是因为丢弃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属性,把“教育”异化为“无产阶级政治”及其“工具”。岂会成功?以至于钱学森临终还在发问:“我们为什么总培养不出‘冒尖’的人才?”——谁说不是呢?在日寇入侵那样的战争动荡岁月,西南联大在颠沛流离中还培养出一批至今彪炳史册的大师,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却反倒培养不出“冒尖”人才,看看西南联大的办学,答案自在其中。听听钱老临终前对于自己留学时教与学之情境的回忆,答案也在其中了……还要说什么呢?
● 社会对人才评价、使用的标准始终制约教育
这应该是一条铁律——正如社会对任何事物的评价标准,都会对该事物的变化发展具有导向、激励功能一样。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要走向社会的,社会要用什么样的人,教育如不予适应、配合,教育如何生存?社会用人看重什么,教育必会追求什么,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倘若社会对人才标准出现重大偏差,如果教育者欲坚守教育规律,那么这样的教育者要么须痛苦地挣扎,要么则被迫离开教育。
当我们从文革“知识越多约反动”的反智主义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端重视学历,乃至视学历(且瞄准全日制高校、名牌高校本科以上)为人才“准入证”时(尤其是地位高待遇好的部门);当招洗菜工、保安也要求本科学历时;当公务员招考将夜大、电大、自考学历都拒之门外时;当用人对实际能力、创新意识的考查不被重视甚至退隐不见时——我们的学生、家长乃至学校岂能不为考试分数及一纸文凭疯狂呢?摧残学生的“应试教育”怎么会退出教育舞台?“择校热”怎么可能退烧?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教育病”自然不一而足,层出不穷,可谓“摁下葫芦又起瓢”——档案造假、学历造假、官员到处以权谋“学历”,花钱发表“学术论文”、高校成学历市场,乐此不疲……社会“病”了,教育也会“病”;教育“病”了,又将使社会之“病”雪上加霜,几近病入膏肓……
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外部的社会人才观、用人机制的改革开始,必须走“重视学历,更注重实际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考查,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用人”的路子,而不是先用一纸文凭将人拒之考核选拔范围之外——这,将直接制约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这需要教育与社会、政府的联动,以形成机制和风气,并非仅“教育改革”可以奏效。(例证——点击笔者《从中美招聘启事的不同说起》一文)
● 要始终把握教育与人、与社会的关系——首要规律
教育是为“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的,教育的追求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这便是首要的客观规律,是教育的总规律,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社会由“人”组成,没有“人”即没有社会。教育是培养人的,而不是培养某种“工具”,更不可能是为了教育事业自身“经济效益”,教育不能成为“商品”。在和平建设时期,当教育有助于“人”的健康、健全发展,必同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教育是可取的,与社会这个大系统是和谐的。反之,如果教育已经明显影响到人的健康、健全发展,那么也就必然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那种教育一定是有病了,必须找出病根予以疗治。那么,当下的教育,有多少成分是在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呢?或者说我们是在培养怎样的“人”呢?我们有多少学校是扎扎实实在培养健康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有学识、有能力、有正义感、责任感、有担当、自信自立、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创造意识的“人”呢?有许多学校难道不正在培养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
健康的社会需要健康、健全的人,教育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发展为本,而不可能是以“升学率”抑或“黄金屋、颜如玉”以及获取“文凭”为本。
如果我们的教育是以获取教育者自身功利为本,或者说以帮助受教育者去获取功名利禄为本——甚至堕落到只是为了让受教育者为获取一纸文凭而应付几张考卷的答题——这还能称为培养“人”的“教育”吗?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成为具有自信、乐观向上、勇于实践创造、有正义感的大写的“人”吗?君不见,在高校积极“入党”的一些学生,竟明言那只是为了谋取就业的优先而已……如此,我们的社会会怎样呢?教育界和社会怎能不“乱象”环生?诸如乱收费、校长腐败、学生没了休息日、压力重重精神抑郁乃至跳楼卧轨、家长教导幼儿园小孩子从小就以上大学为自己的“理想”甚至是“终极目标”、大中学生弑师案耸人听闻、高考舞弊案越做越大、学术腐败、学历造假成为产业创造黑色GDP ……
“前30年”,教育异化为“政治”;“后30年”至今,教育异化为“功利”及谋取功利的“敲门砖”。“教育”的本质属性和规律都不见了踪影。如果“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塞进任何其它的东西,怎么改,都不会成功。
● “教育”与“文凭、功利”及“经济”的关系
笔者也食人间烟火,当然知道没有“钱”无法办教育,而《教育经济学》这门边缘学科的存在,也证明“教育”与“经济”是有关系的;笔者更知道即便再重视实际能力和创新素养的考察,学历也是重要的,它证明某人曾受过怎样一种系统的教育和知识结构状况,在同等能力水平上,高学历者肯定占先。那么,如何看待“教育”与“经济”与“文凭、功利”的关系?
教育需要投入,但教育自身不应成为“挣钱”的机构,或部分参杂“挣钱”的功能,因为这不是属于“教育”的任务——那是企业和国家税收的事。
“教育”不“挣钱”,而是培养“人”的。但它在客观上同样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而且是难以计量的财富——“教育”培养出“冒尖”的科学家或一般的创造性人才,他们创造的财富正是难以计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经济学》。说钱学森“手无缚鸡之力”也许不为过,但美国人却说他抵得上 5 个师。此为挂一漏万之一例。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获得仅其可能的健全发展,这是始终不渝的。“文凭”只是某学校给以受教育者最终的学历证明而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将获取这一纸证明视为教育和受教育的“目的”,将“人”的健全发展这一根本置于获取“文凭”的从属地位甚至忽略不计,这无疑是本末倒置。教育的异化从这里开始了。
同理,因受教育获得发展,真正成为社会需要的人,于是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和待遇,这是自然的结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果将获得报酬、待遇作为教育的“目的”,这又是一个本末倒置——以此为“目的”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绝对培养不出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人”——因为“目的”的错误一定导致手段、过程、策略的错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在这样的人心中除了“报酬、待遇”,难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和具有一定风险的创新精神。
● “教育”与“人才分布常态”和“社会发展”趋势须适应
即使在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还是要从事普通职业——即稍微简单一些的劳动,如技术工人、普通工人、懂得现代农业的农民或曰农技人员、农场管理者、各种操作员、售货员、公司职员等等……除了文教卫一类专业性强的行业,大多并不需要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这是符合“人才分布常态”和社会发展常态的。那么,在我们这个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不是应该大力兴办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中等的或稍高等的?是不是应当鼓励一些企业招聘降低“学历”门槛而加大实践考察的比重,以最终形成重能力考察而参考学历的机制与风气?并以此促进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和学生素质提高?普通劳动者素质提高了,整体国力的提高也就在其中,而且是终极性的提高。
社会重学历而忽视实际能力的考察,导致盲目“大跃进”式的办大学搞“扩招”,导致大学教学质量下降,导致手持高教文凭的学生却“就业难”,甚至手持硕士文凭去应聘各种简单体力劳动岗位,如卖肉洗菜;可也在一些地区出现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企业简单劳动的岗位却“招工难”这样的怪现象。这能说我们的教育发展理念和教育结构正确、合理吗?这能说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状态和人才分布的常态吗?在这里,“科学发展观”哪里去了?
从人格、人权而言,人与人是平等的;就能力、才智而言,人和人自然是不同的,连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一点,多元智力理论更对此有科学的阐释。世界上没有绝对同质的两个人,必各具先天禀赋、个性特征的差异,有些人适合做学问,有些人艺术创造、表现方面更有禀赋,有些人动手操作特能干,有些人过目不忘的能力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为什么不能从高中开始逐步分流呢?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因材施教”,可我们为什么都朝着应付高考几张试卷的一个模子去培养学生呢?——哦,因为我们的人才市场、用人单位、组织部门绝大多数是以大学本科乃至硕士文凭为“准入证”的,且有时连国家承认的电大、自考等学历也不认!水平再高、能力再强,学历若不“达标”就甭想进入某种阶层或领域!为此而破格录用的例子简直如凤毛麟角!所以,社会用人机制和观念,是制约教育改革以及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瓶颈。
德国是科技和制造业相当发达和先进的国家,尤以工艺精密见长;而他们的高中毕业生大约只有30 ~40% 去读普通大学本科,其余皆进入各种职业学校和学院。所以,他们制造的产品都很精细、精准,这源于他们有高素质而并非高文凭的劳动者。当中国派出代表团去考察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经验时,德国人却说他们最初是向中国已故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学来的。这怎么不叫人无语?!(参阅《陶行知研究在德国》)
中国的教育资源只占全球的 3%,但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虽然中国目前(2010年)全国大学的入学率是百分之二十多,但这是平均数,在大中城市,高中生大学入学率已达到 90% 左右。可是,这符合社会基础的客观状况和人才分布常态吗?这与社会需要适应吗?当手持本科、硕士文凭的年轻人,却干着售货员、保安员、清洁工这些简单劳动时,我们难道不感到是对国家和他们个人的教育投入极大的浪费?诚然,我们不否认这之中某些人在将来的发展中,他们在大学所学知识会发挥作用,但就整体而言呢?
● 规律告诉我们:“择校”永远消除不了,但“择校热”完全可以降温
将解决“择校热”和乱收费的途径单一归为“均衡教育资源”,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
“择校热”和高收费乱收费可以消除,应该消除。但是“择校”,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已经存在和必然继续存在的现象,可以说永远消除不了,只是程度会有不同而已。教育再怎么做到均衡发展,都无法做到学校之间没有差距。这是事物多样性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的。好差优劣是在比较中产生的,有两所学校存在,就会有差别存在,人们就想选择其中一所自己喜欢的或适合的学校,何况,择校还会有所谓挑选好学校以外的其它原因存在。
“孟母三迁”虽非为“择校”,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择校”的原因。这是规律之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择校”和“择校热”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呢?难道均衡教育资源配置了,“择校”现象就没有了吗?面对无法回避的现象,就必须有合理的对策来引导和规范它,否则还是会混乱。这是规律之二。
其实,“择校”是在择“优质教育资源”即所谓“好学校”吗?非也。正如湖北省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邴俊英一语道破: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主要是择初中学校的优质高中升学率——那么高中择校自然也“择”的是高考升学率——与“优质教育资源”没太大关系。”著名”的高考工厂——安徽毛毯厂中学就是一例。把“择校热”笼统归结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或“不均衡”,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片面的;同时,对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也缺乏明确的认识。比如,那所“安徽毛毯厂中学”,还有许许多多以高考升学率为金字招牌的“省级示范高中”,它们是”优质教育资源“吗?
当组织部门和社会用人机制、人才观转变了,当“文凭”不再是人才市场唯一“准入证”时,当“不拘一格降人才”已成风气时,尽管“择校”现象还会有,但那已经属于“常态”、常规,“择校热”、乱收费自然降温乃至消失。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应当是有关消除中国“择校热”的规律之三。
● 一 线 曙 光
拉拉杂杂想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一则报道:有一个城市在尝试“教、考(高考)分离”——即高中毕业考试后,学校不再组织高考的事儿,由学生自己到社区去报名参加高考或者直接就业;而上级对学校办学水平的评价主要在于校风、学生反馈和办学过程行为的评估考察(包括全省毕业会考成绩)——窃以为这不失为促使教育返璞归真的一种尝试;其实过程如果是堪称科学、合理和优良的,结果能差到哪里去吗?——这倒有点像是办教育了。笔者觉得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一线曙光”……
今天“断想”暂时到此。□
2010年3月 / 2016年6月 修订
| 【本站最近相关更新/最近评论】 |
||
〖前一页〗 1 〖后一页〗 |
||
| (本站 2010年3月18日 编辑发布 / 2020-08-12 再次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