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重读历史>沉重的1957-1965>【胡平/著】残简:1958(转载/在线阅读)-P.3. | | 您好!今天是: | |
 |
|

| 【“反右运动”· 历史的报告】 |
|
| · 胡 平 · |
| 作者:胡 平 资料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等 本站编辑转载(本页浏览:人次) |
点击下面目录,浏览相关内容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六、命运倘若不那么正经
1958年里,还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实施劳动改造。
一天深夜,因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叫嚣”而惊世骇俗的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人民大学的家中带走,收押进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看守所,春节后开始对他进行了第一回合的审讯,这一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审讯,共进行了36次——
“1938年你在河南商丘组织了游击队,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打日本鬼子。”
“胡扯!当今人民坐稳了江山,你还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人,那时你怎么可能将枪口对着日本人?”
“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时搞策反,解放战争时奉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不准你再用自己的罪恶玷污我们伟大的党!我警告你,这里是清算罪恶的审讯室,不是可以信口雌黄的江湖码头,你若再不老实,就得罪上加罪!”
命运这家伙,倘若正儿八经起来,你便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倘若不那么正经,有时还要黑色幽默一下,本该大红大紫的你,却可能灰头垢面;如涸辙之鱼。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葛佩琦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入该组织,又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黄华、姚依林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便投入了党的秘密工作战线,抗战时期孤身策动伪军一个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人我抗日部队序列。解放战争时他前往沈阳,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通讯处长。
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在通辽一地他曾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的智商,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的,可当年葛佩琦还是一次次金蝉脱壳、化险为夷了,他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而眼下,他却被几个党龄比他短得多的共产党员们“识破”了面目,他们无须懂得任何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只需凭着锋利的权力之角,眼里火焰般迸射的阶级仇恨,便能将他牢牢地抵牾进死角!
“虽然我在东北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同志,在西安陷入了敌人的魔掌,押送南京后又下落不明,但是这个情报组一定还有同志健在,你们应该赶快去调查……”
葛佩琦一遍又一遍的诉求,哪怕是一堵墙也应该听进去了。然而,对方觉得,对于一个右派分子,赶快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调查他曾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得让他从此后不再能做什么,能说什么。
1958年下半年,葛佩琦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投进山西省第一监狱服刑。
七、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
有一种文化形态,它绝对不像“中学为本”一样,散发出沙滩上死鱼的腐臭气息。它也运筹帷幄,殚思极虑,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锯一一去锯断从政权到文化、从经济到风习……这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种种制度。当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它期盼在封建社会的坟场上,崛起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它也不像“西学为体”一样,隔着大洋抛洒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惧西方现代文明,多少年里,这文明总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穿着一条连裆裤。它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邪派高手一旦进来,便会一脚踢翻中国这只布满小生产者的马铃薯的口袋。贫富不均由此派生,尔虞我诈由此繁衍,男耕女织将何寻?田园牧歌将安在?
它像个诗人,充满诗意地描绘着中国的出路:
一边彻底地抛弃封建社会那又长又臭的裹脚布,一边断然杜绝西方现代文明那光怪陆离的霓虹对我们社会和伦理的诱惑。以自己的文明资源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跨越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它像燕子筑巢,严格地在两类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里,选择着自己的载体:
它看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招魂扬幡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封建社会躯体上见头上有肉就去舔头、头上烂了就去舔脚的一群跳蚤。19 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凡俘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仪者,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在时代的暗房里,他们在进口的胶片之上,冲洗出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国的嘴脸: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平均主义……
他们将胶片踩在脚底下,冲出暗房,好似冲出一个幽深漆黑的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没有比卢梭、华盛顿、法国革命纲领、美国独立宣言,更能让他们感 到长风惊耳;也没有比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使他们觉得阳光如瀑。为了这片古老而又苦难的土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甘愿走上险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个任凭鹫鹰叼啄心肝也要盗得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只要秦皇汉武,还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却长久地不需要普罗米修斯。
在 20世纪最初的十年,从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虽然以彗星般夺人眼目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可终归也如彗星一样,很快便和他们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坠落在长夜难明、云厚天沉的封建晴空里……
知识分子是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比起单纯的“面条”来,“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嘘、太多的动摇,自然也有太多的主意、太多的躁动、太多的探求。
前者犹如一个“郊寒岛瘦”迎风落泪的弱者,人们很难喜欢。难怪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虽说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掌了大印的王明、张国焘就宣布要“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他们视自己的同类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险分子……
后者则像一个思绪如梭、才智逼人的强者,人们更难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后,将可能划破正进行庄严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让观众看到布景后不那么庄严的东西……
林黛玉决不会去青睐马房里的焦大——这种文化形态断不会寻知识分子作自己的载体,由此也是确定无疑的了。
剩下的一群唯有非文化人,在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弱小的情况之下,他们主要当然是农民。似乎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强选择,其实正是门当户对、珠联壁合的联姻——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金戈铁马声中,我们听到了农民对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断然革命的要求。但这一要求绝不会引起中华文明的巨大断裂,我们拂去历史弥漫的烽火硝烟,不时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旦冲进了紫禁城下,便要黄袍加身、分封诸侯,而不会厉兵袜马,再展长缨,席卷巴士底狱、凡尔赛宫,并迎风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来……
农民虽然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条刷在土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握缨而起,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他们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说知识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罗飞船登月,那么农民的渴望只是借梯子上墙,后者不但渺小,有随时实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剧烈震荡。墙外也只是少有变化的炊烟与村庄,小溪与山岗,可月球上却绝对是反差强烈的气候,完全陌生的地况地貌。
农民动如脱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极大的革命动力,可一旦满足了生存需要,顷刻间便静如处子。农民能去疆场上出生人死,却不会去从思想上出生人死。他们的思想得有人规范,一旦被规范,他们则终生难以逾越。因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紧密联系,农民安道守常,循序渐进,他们是民风醇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稳定的磐石……
犹如无垠、丰饶的尼罗河流域,托起了辉煌、雄伟的金字塔,中国的农民完美地托起了这一种贴近乡村的文化形态。而这一种自然远离城市的文化形态,也用一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精心包装了农民的理想与农民的哲学。
八、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1958年8月4日,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
毛泽东的专列由北京站徐徐驶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县。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徐水县委做了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大部分劳力和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他老人家视察的地方,并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团、营、连、 班、班,哪一级出了问题,找哪一级的头头是问。道路两边的庄稼不得有一点杂草,地里有人干活就得要有红旗飘扬。县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均被打发去偏远的地方下乡……
对伟大领袖的敬爱是真实的,对伟大领袖的蒙蔽也是真实的。一切细节的安排,都好像出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在看了路边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一块庄稼地里两座正呼呼腾焰的土高炉后,毛泽东走进了一个干净得几乎一尘未染的院落,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它的四面墙上,除了窗子,被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计划图表和上级下发的大跃进宣传画所淹没。在这里,毛泽东问该社社长:
“你们农业社叫个什么名字呀?”
“叫第八渡河农庄。”
望着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四面墙,尤其是宣传画上那攀着玉米秸子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壳作舟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老汉,还有农业社的地里采摘棉花的媳娥姑娘……毛泽东一定呼吸到了在北京城里很难呼吸到的、来自广安土地和庄稼的灼热流风。
对于一位农民的儿子,并终生关注着农民命运的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像这一股股热风,升腾起他胸中的激情,他大概想起了八十七年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犹如他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跟着赫鲁晓夫后面亦步亦趋一样,他也不想让中国的农村再重复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他说: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当社长告诉毛泽东,今年麦收亩产达到754公斤,县委书记又汇报到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 2000斤、总产要达到12亿斤时,瞪大了眼睛的毛泽东,和县社干部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够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在人们众星拱月般的簇拥下,毛泽东又去看了社里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将土堆积成小山状、据说亩产可达120万斤的“山药山”。33岁的县委书记一路滔滔不绝,向伟大领袖介绍这些新事物、新创造,水浪一样波动的舌头不打一点颤,既然《人民日报》连日来发表社论,批判“有条件论”,号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的舌头又怎会去打颤呢?
毛泽东的思绪也滔滔不绝,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何曾有过为了粮食太多而发愁的日子?面对一张张激动而又木油的庄稼人的脸,他高屋建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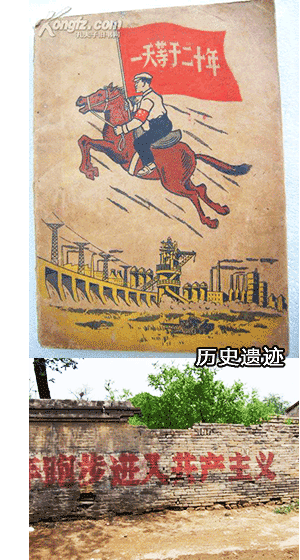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据新华社报道,所经之处,无不一片丰收景象,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无不热气腾腾。他在被“大跃进效应”深深陶醉的同时,又在各地更广泛地撒播了“大跃进效应”,以徐水为例——
他离开的次日,县委召开全县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其后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口、房屋、树木等均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人社折价款决定取消,各公社实行或准备实行工资制。
他离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怀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来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的试点。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中央、省、地和县各级一百多位干部组成的班子,对徐水的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田园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拿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又在一个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这一试行草案规定,全县公民“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于是,家家砸锅炼铁,户户不再冒烟,人们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饭,就连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为了根除私有制,干部的工资停发。改为津贴费,县级干部每月9元,科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每月2元。在搞得彻底的地方,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为公有,可以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的都归公了……
在此基础之上,9月间,成立了实行县社合一的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在设置有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治公安部、军事部、工业交通部、农田水利农业部、妇女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15个主要部门外,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道,内称: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上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想必这是原本在中国当代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徐水一段最风光的日子。
这风光来得如此迅猛,如刚刚还是晴空朗朗的平畴上兜头泼来的滂论大雨,让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可它又如此真实,每日里车水马龙、黄尘滚滚,全国各地来此朝拜共产主义“麦加”的人们似过江之鲫,仅至10月底,来徐水参观的外宾就有近千位, 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
那些日子,徐水的老百姓,多半是在一种半是梦幻、半是现实的状态里生活,说是梦幻,除去扛枪当兵或是落草为寇外,吃饭不要钱,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情;说是现实,每日里走进食堂,面对一桶桶白花花的馒头、米面,你敞开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对于敞开胸怀尽情拥抱风光和荣誉的徐水各级干部来说,他们则大体上处于一种没有喝酒却似喝了酒的醺然状态,除了自己姓甚名谁没有忘记以外,多半他们已经忘了这是在还一穷二白的中国,这是在泥屋、柴棚还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为是在十月革命之夜那灯火辉煌、万头攒动的斯莫尔尼宫……
(未完-点击:接下页)
【相关链接】
1、【历史解读】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制度的“大同思想”渊源(文/凌志军)
2、【搜狐大视野】“天堂”实验: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记录与述评)![]()
3、【史料】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 风 破 浪(大跃进的号角)
4、 林蕴晖教授主讲:1958 年的“大跃进”【历史讲座视频】![]()
5、 林蕴晖著《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
7、 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10、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和学校
12、张一弓1980年获奖小说:《罪犯李铜钟的故事》(纪实性小说)
13、【本站编辑】“人民日报”上的“整风-反右”历史记录(鉴赏“右派”言论)
【附】 【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建国60 年纪事】目 录(选)
|
|
||
| (本站 2008.05.12 编辑转发 2018-11-29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