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历史钩沉>韦君宜:《思痛录》>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 | | 您好!今天是: | |
 |
|
|||||||||
点击这里展开:韦君宜简介——
韦君宜,1934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中共进入北京建政后,韦君宜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9年初,韦君宜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带职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参加编写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 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离休。 1986年4月起,韦君宜因中风卧床,病中克服重重困难,一直笔耕不辍,不但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思痛录》,而且,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抗战时期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也在1993年初脱稿。 仅看以上简历,似乎韦君宜一路顺畅,其实不然——每个人的几行“简历”背后,都有着许许多多感人的或匪夷所思的故事,那便是历史,其中也许有欢笑,有阳光,但无疑也会饱含血泪,有说不尽的心痛和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些,是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因为,任何社会、国家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必然都留有历史的印记,不了解这些“印记”,那只能算糊涂虫,并且一定会迷失前行的方向和正确的价值选择。这些,岂是“简历”中可以容纳得下的? 2002年,韦君宜因病去世。韦君宜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撰写回忆录《思痛录》,因为它多少能使我们拨开历史雾霾,一窥其庐山真实面目——起码是真实面目的一部分。 韦君宜女士,安息!历史和人民将铭记和感谢每一位董狐笔!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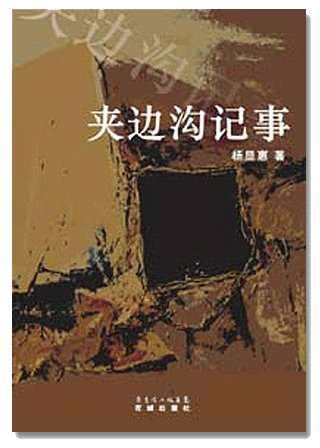
点击:到本站“重读历史”专栏
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 |
| 作者:杨团 来源:《二闲堂文库》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
【本站按】 有人称其“自干五”且头上有着一大堆耀眼光环的王绍光教授,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王绍光谈整风反右》一文中如是说:“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矛盾就用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逻辑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说得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个逻辑一切都说不清楚。” 读王绍光此言,不禁令人哑然失笑,难怪有人称其“自干五”。《思痛录》一书的全部历史记忆和成书到出版的始末,难道不充满了历史的荒唐和疯狂?有几人能指出这本书有多少不实之处?这其中就“没有谁对谁不对的问题”?王绍光是否想说这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正义、公理及与其相对的邪恶与荒诞? “文革”折腾了好几年,把刘少奇打下去、折磨致死,把林彪树到毛“最亲密战友”、副统帅、毛继承人的地位,可最后这位被国人每天“敬祝永远健康”的毛之“最亲密战友”却驾机叛逃国外,弄得毛无法向全党全国交代伤透脑筋,大损健康,这还要如何荒唐、疯狂?这反映了怎样的“逻辑”?直至几年前,重庆那位薄氏书记,其妻杀人越货,然后薄一耳光把他的属下重庆市公安局长打到美国领事馆里去“避难”……这还要多荒唐、疯狂?王绍光,歇着吧,当“自干五”也得看看说些什么话题啊!历史岂是你要颠倒就能颠倒的?历史是客观存在,不是王绍光巧舌如簧的说词。仅就笔者信手捡来的几件,有哪一件王绍光能给它来个“颠倒”并“说得清楚”?不过,也许王绍光说得也对——这里面都是有“内在逻辑”的,那就是专制独裁政权的逻辑,就是宫廷厚黑政治的逻辑! 我们还是静下心来,读读韦君宜这位延安老革命的遗作《思痛录》,读读这本书成书的始末,就能看到王绍光本人倒是多么荒唐、疯狂和可怜、可笑! |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从美国归来。下飞机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的《思痛录》样书一下子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我把这本薄薄的小书宝贝似地捧在胸前,深深地呼吸着,只觉得油墨的芬芳沁入心脾,眼前又浮现出病榻上的母亲紧眠着嘴唇,悲哀地望着这个世界的面容……不觉得眼眶湿润了。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您2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何止二十年,是整整半个多世纪,您和您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啊!
一、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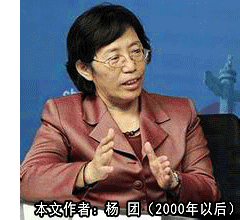 记得那是文革中期,一九七三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一九六六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七年,到一九七三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二十四小时连班(化工反应釜需要仪表持续监测,仪表修理工每值二十四小时班可休息一天),觉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线,来回颠簸整整十三个小时赶回到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小屋里。
记得那是文革中期,一九七三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一九六六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七年,到一九七三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二十四小时连班(化工反应釜需要仪表持续监测,仪表修理工每值二十四小时班可休息一天),觉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线,来回颠簸整整十三个小时赶回到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小屋里。
当时我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
父母告诉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原来那时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我听了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敌人越多党就越安全吗?”
记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驳的语言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团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这话一下子震惊了我,迄今我还记得她当时脸上的表情,记得我那莫名的惊诧。
我的妈妈呀,竟会怀疑她的女儿会出卖她!自然,后来我就努力多听、多想,插话也大都是问情况的了。我就是这样听到了所有后来被母亲写入《思痛录》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越讲越长,从打“AB团”,延安审干开始,讲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轻骑兵”,解放后的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一系列曾经冤枉过人的运动,也包括大跃进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种种。让我听了震惊甚至恐惧的还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苏共二十二大,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斗争,以及中苏两党在整人上的惊人的一致和从建国前就存在着的矛盾。说老实话,我的真正的大学是在那四年(1973-1976)完成的。如果说文革头七年的遭遇和磨难是锻造我意志的铁砧,那么,后四年的家庭讨论会则是开启我心灵的钥匙。我至今怀念那四年白天盼着天黑,吃过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台灯前,同志加亲人的热烈而又有点神秘的讨论。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萌生了要写一部书的念头。她当时常常对我讲,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多灾多难,交到你们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早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四清。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把学部当天所有的情形都对我这个当时才上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统统说了。我那时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但是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此生此世铭记在我心里了。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不起今后的生活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直言:“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也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同志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当时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怕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谎言,1943 年共产党就能把才二十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十七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三年才能解决。结果,连他自己也未料到,这一次的平反竟拖了整整十二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当时的我,突然遭遇这一切,一下子懵了,哭着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绻缩在藤椅上睡着了。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一下子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因为他对形势的估计非常险恶。他唯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从此几年不见家人面,再也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唯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有这一点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做遗言在讲。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一下子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因为他对形势的估计非常险恶。他唯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从此几年不见家人面,再也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唯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有这一点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做遗言在讲。
到了 1973 年全家重新聚首时,父亲讲述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壮到极点的气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讨了,而我的认识仍然幼稚之极。也许正是从我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亲和父亲一样,痛切地感受到了对年青一代“愚民教育”的危害。为了免除子孙后代因无知、盲从重蹈他们那一代的苦难,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记住那一段痛彻心脾的历史,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时,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一整代共产党人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如实记录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人的想法在她脑海里成形了。
二、母亲写《思痛录》
《思痛录》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据我回忆,是在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帮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
当时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但是军宣队还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经常出差,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写作。偶尔写一点她也从来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经常随便拾片纸就写,还特别爱用那种没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纸。可是,有一段我却发现她写东西有点不同往常。她写在16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迭稿纸上,每逢吃饭,出门都把稿子放在书桌旁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母亲写东西如此保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记不得过了多久,也记不清是她先告诉我还是被我自己翻到了,我知道了这就是那篇“抢救失足者”,后来被收入《思痛录》作为第一篇。
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我活着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写完了你一定要给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总是不相信,怕我马马虎虎,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在她心目中,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点 击 图 片 , 进 入 本 书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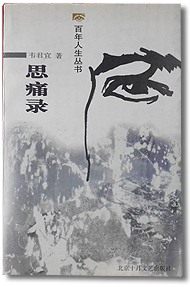 |
||
| (本站 2006-04 编辑转发 / 2017-12-25 更新)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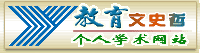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