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历史钩沉>韦君宜:《思痛录》>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
点击这里展开:韦君宜简介——
韦君宜,1934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中共进入北京建政后,韦君宜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9年初,韦君宜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带职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参加编写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 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离休。 1986年4月起,韦君宜因中风卧床,病中克服重重困难,一直笔耕不辍,不但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思痛录》,而且,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抗战时期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也在1993年初脱稿。 仅看以上简历,似乎韦君宜一路顺畅,其实不然——每个人的几行“简历”背后,都有着许许多多感人的或匪夷所思的故事,那便是历史,其中也许有欢笑,有阳光,但无疑也会饱含血泪,有说不尽的心痛和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些,是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因为,任何社会、国家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必然都留有历史的印记,不了解这些“印记”,那只能算糊涂虫,并且一定会迷失前行的方向和正确的价值选择。这些,岂是“简历”中可以容纳得下的? 2002年,韦君宜因病去世。韦君宜生前用她最后几年的时光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撰写回忆录《思痛录》,因为它多少能使我们拨开历史雾霾,一窥其庐山真实面目——起码是真实面目的一部分。 韦君宜女士,安息!历史和人民将铭记和感谢每一位董狐笔!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点击:到本站“重读历史”专栏
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 |
| 作者:杨团 来源:《二闲堂文库》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一九八六年初,已经六十八岁的母亲才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了她的离休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她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她似乎有些接受不了自己退出社会主流生活的事实,整天还在盘算要到哪里出差,要做些什么事情。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四月间的一天上午,当她在作协召开的一次文学作品评论会上发言,手伸向茶杯正要举起喝口水的当口,突然茶杯哗啦一声砸在桌上,她两眼一闭,人事不省了。等我赶到协和医院,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她已经被送入病房紧急抢救,仍然未醒过来,被大夫诊断是脑溢血。她的出血部位是在左脑,CT片子上核桃大小的出血痕迹赫然可见。后来大夫告诉我,这个部位出血,况且又有这么大面积,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她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而她居然恢复到能走路、说话,甚至还能写作,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医学上无法解释。如果要解释,只能说她是作家,终日用脑,所以大脑功能被破坏后的恢复和一般人不同。
当夜我一直守在她身旁,到夜里12点多钟,在药物的帮助下,她那顽强的生命终于苏醒过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一定是听见了我在她耳边拼命地叫喊,努力撑开眼睛,认出了我,然后艰难地卷着舌头翕动着嘴唇。我竭力分辨那模糊的发音,她是在说:“我完了,我不行了。”我一下子哭出来:“妈妈,你总算活过来了。”
三天后,当她完全清醒了,就立即开始了那顽强到残酷程度的自我训练。每日记着数刻版地练习抬手、抬脚、握拳。为了能再继续持笔写作,她让我买来小学生用的格子本,说“我要从一年级上起”。她僵直的手指完全握不住笔,第一天练习可谓一笔上天、一笔入地。不过练习极为见效,那四个被她在封面上填上一至四年级的练习本,是她恢复书写能力的见证。第一页上满是歪歪曲曲的笔道,以后就像一两岁小孩画画,再以后就勉强可以辨认字形,最后的几页甚至于可以看出一点昔日的笔体了。那本子上写满了唐诗宋词,而且居然一首都不重复。一个月后,她开始下地练习走路。三个月后,大夫就说可以考虑找个康复院练习功能了。我们实地去调查了一阵,最后与母亲共同商定,选择了北京郊区新开的一间民营康复院,把她搬了过去。她到这间康复院大约在8月间。入院的第一天,她就把所有的功能训练器械统统尝试了一遍。拄着拐杖在楼道内咚咚地急迫地走着,不让我扶她,那情势好像她的心跟着拐杖把步子先于自己的脚迈出去了似的。在这间康复院她一直住到冬天,直到天太冷取暖设备差不宜再住才离开。后来,她写出反映她在康复院生活的散文──《病室众生相》。当我读到这篇散文时,真的大吃一惊,我惊异劫后余生,重病在身的母亲居然能如此迅速地恢复了脑力,这一篇的笔力与她病前作品的差别,不很熟悉她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三、母亲的遗嘱
一九八六年深秋,一次,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讲:“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的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强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也许还在思想。
这两片纸被我好好地保存着,看到它,我就觉得人生无常,人事无常,不觉悲从中来。母亲的遗嘱分为“我的作品”和“我身后事”两个部分。作品又分为“我的小说集”、“散文集”、“杂论集”和“我的回忆录”。今天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她当年所有的愿望,如今大都在她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实现了。特别是在1987年后,她不仅又写了十余万字的散文随笔,还以病残之躯,完成了“抢救失足者”的姊妹篇十余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并先于《思痛录》于一九九四年出版。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住手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个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蹉商每一章的名子,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读懂全书后痛彻的共鸣。所以在1997年当林文山同志拜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八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就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八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期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编辑《思痛录》,我尤为认真。每一篇都读,有时会讲点感想给母亲。那八章以外的各章,哪篇宜放入,哪篇不宜,也进行讨论。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个别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有时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记得《思痛录》的头几章也是经过了修改的。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孙友余同志要我向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同志引见一机部派出的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法学硕士。由此有了我和母亲与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亲后来帮助他解决了被人冤屈的事。交往当中,这位唐先生曾亲口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当谈到那一段历史,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而且当下就真的点出几个人来,说是这些人如果来美国发展,那一定会有辉煌成就。
唐先生走后,母亲和我谈了很久。她谈到她的父亲──我那曾经第一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母亲赴美深造。这机会被母亲弃之如敝屣,她义无反顾奔向了延安。谈到我父亲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但为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他“已悔名山不朽业,志坚意决报邦家”;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彬、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最后母亲竟唱起了当年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与唐先生的谈话及母亲的感慨后来被添入了《抢救失足者》一章。
四、未收入《思痛录》的痛思
在编辑《思痛录》时,母亲教给我许多编辑的知识,选稿的标准。我提出既然选入了李兴华的那篇《一个普通人的启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选入另外两篇写人物的,为什么要添上“取经零忆”等等。她的回答我以为都很有道理,自然照她说的做。但是,唯有一件事我与母亲争执不下。而当她已经不可能再自行管理自己的作品,必须由我处理时,我违背了她的意愿。 我真正行使我的“代理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母亲写于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那首诗拿出来发表。
那首诗是在她重病以后,我为了整理她的所有文稿,彻底清查文件柜时翻出来的。它夹在父母从解放区带出的报纸杂志里。居然能逃过文革多次抄家的浩劫保存至今,简直是奇迹。不过,我以为这批材料早就被抄走过,是一九八五年中央办公厅清查文革旧档案,特别通知家里去领父亲的材料时退还的。诗被母亲用蝇头小楷竖写在延安出的马兰纸上。那纸不算薄,暗灰色的一卷,叠成三十二开大小的五页,周围已经磨起了毛边,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母亲的一卷诗里还夹着一张薄薄的似乎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黄纸片,上面也是一首诗,有红蓝两种钢笔字,可见书写时的局促。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父亲的字迹。第一次读到这两首诗,是在1986年冬天。屋里生着暖汽,外面刮着寒风,读着读着,我的心被攫住了,颤抖得像寒风中摇曳的枝丫,待我镇定下来,已经泪流满面了。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点 击 图 片 , 进 入 本 书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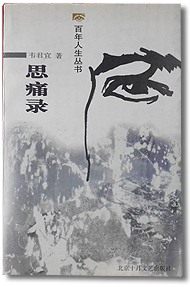 |
||
| (本站 2006-04 编辑转发 / 2017-12-25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