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本站评论>【本站评论】现代汉语“X+化”派生词的语义变化——兼议“×××主义中国化” | | 您好!今天是: | |
|
||||||
|
散文 小说——
视频、时评、重读历史:
说说现代汉语“X+化”派生词的语义变化 |
|
|
|
· 应学俊 · |
|
| 原发“博客中国”网站 (2016.2.27) 作者2018.10.24修订 本站发布(浏览数: 人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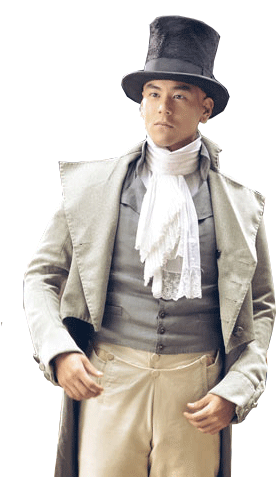 有这样一个场景:A先生到英国留学、工作以致定居,20来年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在一次老友、同学聚会以后,朋友们都说:“A先生简直完全‘英国化’了哦,穿着打扮、一举手一投足,动辄耸耸肩膀摊开双臂,乃至价值观、思维习惯等,真的‘英国化’了!”有个别人甚至不屑地说他是穿着西装的“假洋鬼子”……
有这样一个场景:A先生到英国留学、工作以致定居,20来年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在一次老友、同学聚会以后,朋友们都说:“A先生简直完全‘英国化’了哦,穿着打扮、一举手一投足,动辄耸耸肩膀摊开双臂,乃至价值观、思维习惯等,真的‘英国化’了!”有个别人甚至不屑地说他是穿着西装的“假洋鬼子”……
窃以为,背地里如此无端地似乎不友好地议论人当然不可取。20多年生活在英国,是难免不被“英国化”的。
可是,说到“英国化”,笔者却联想到在汉语中,“化”除了本身的词义外,它还是个具有很强构词功能的后缀字,比如:西方——西方化,中国——中国化,信息——信息化,机械——机械化,革命——革命化……“X+化”的派生词可以说举不胜举。
※ 略谈实词加后缀“化”——语义、概念产生的变化
带后缀“化”的词几乎每天都在增加,故也几乎不可能穷尽考察。汉语言学里一般称之为“‘化’尾动词”或“‘化’尾名词”。再举几例,如:汽化、老化、退化……美化、神化、绿化……规范化、现代化、大众化、国际化、信息化、时尚化;还有主谓结构的“体制僵化,机械老化,水质净化、家居智能化”……可谓不一而足。但显而易见的是,“X+化”以后,其语义、概念是有显著变化的,这在实践中有迹可循,有案可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客观实践告诉我们:某些实词加上“化”尾词缀后,就表示具有某种人或事物“转变成另一种性质和状态的人或事物”或者“向某种性质和状态发展变化”,其原有性质、状态发生了明显的较大改变——不论是静态的还是进行状态中的。比如,“他完全‘英国化’了”,其含义显而易见,亦即除了他的祖籍和华人DNA及五官特征外,其它皆与英国人差别不大了。水塘里浑浊的水,通过“净化”以后,其性状、成分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原来的性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水如果“汽化”了,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原来所见的“水”,也不能称之为“水”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城市——城市化(或曰‘城镇化’)”。城市,即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或特大居民区,有比较完备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设施、机制。而“城市化”或曰“城镇化”,则是指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性现状。这里一个“化”,难道不是使原有的概念内涵产生了质的改变?
这种语言现象的规律、内涵虽然还在研究之中,但“X+化”语义变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和规律,是无可置疑的。
于是,笔者不能不想到常听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不免有些心惊。
※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何谈“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不仅诞生于西方,而且诞生于160多年前。遵循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自然要紧密联系本国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死板地照搬教条,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这都毋庸置疑。但既然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那么对它的“发展”和“丰富”必然皆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这就首先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会深透,这是基础和前提。倘若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那么就谈不上“发展”和“丰富”了。(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是的,截至2018年,30多年过去了,我们“搞清楚”了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内涵究竟如何界定?即便有所界定,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联系?
※ 如果连“原著”都远未译完,又如何谈得上“完全搞清楚”?
2008年“环球网”(记者/邵京辉)援引瑞士《基尔日报》报道称:在中国,马克思的著作依然没有被翻译完。这篇外媒引用中国中央编译局的部门负责人蒋仁祥的话:未来18年内有望完成60卷中20卷的翻译。中国目前还没有直接从德文翻译为中文的马克思著作。仅有的《全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俄文转译的中文版,这个版本与原文有出入,不符合科学的高要求。蒋仁祥说道。
| 上述报道网页截图—— |
 |
直接从德文版翻译的马克思著作至今不知已经译出了几卷?倘若已经有了,又有多少人认真研读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姑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却是“二手”的——俄国人从德文翻译为俄文,我们再从俄文翻译为中文,产生错误、曲解是在所难免的了。
※ 还没“搞清楚”就急着“化”带来灾难性后果
例如,张春桥就曾玩弄从俄文版翻译的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讨得了毛泽东的赏识。一个小小的翻译曲解问题,带来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文革”,带来了文革中“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错误和举国的灾难性后果。197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通知,废止了 “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名。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想到此,怎能不有些心惊?(点击参考注释)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是毛泽东提出的,但毛泽东在“文革”中却曾明确批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要求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这当然批得不错;但看来批评的对象却仍应包括毛本人——如上文所述,1958年和后来的“文革”中,毛与张春桥就有意无意曲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等,此仅为一例耳。而实际上,充斥于毛书房的也是中国线装书、中国文化典籍为主;在毛的讲话、论著中引用马列原论也不多见,而引用中国文化典故的倒比比皆是;甚至直接提示、要求某些领导看这篇那篇古文,甚至要求武将许世友要将《红楼梦》读5遍……而极少见毛要求下属认真读马列的什么篇章。
没有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就盲目“中国化”的教训,以上是最典型例证了。
※ “弄通”为基础性前提,实事求是慎言“化”
按照“X+化”的构词规律和语义内涵变化的客观存在,再考虑德文版马克思原著的翻译进展缓慢,没有可靠的文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前提和基础何在?在这种状况下,不是首先像毛泽东所说的“弄通马克思主义”,而是一味追求“中国化”,不知可靠性有几何?再弄出像张春桥搞的那套“中国化”的“法权”笑话岂不要误大事?
看来,汉语“X+化”的派生词在语义、概念内涵变化方面的客观现象和规律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好,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应用”好?这恐怕也是大有讲究而值得斟酌的。
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也会有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老挝化”……化来化去,我们很难说还是不是原来那个“马克思主义”——正如被“英国化”了中国人,除了DNA我们很难说他是100%的中国人了;水被“汽化”以后,我们也很难说飘在空中随时会不见踪影的“汽”就是马上能喝到嘴的“水”。
窃以为,从可靠的文本出发(不是二手的),首先比较系统地弄懂原著和某些基础性概念,然后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异同之处和真实联系——以及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某些论断与时俱进的应有发展,看看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回答当下的实际问题,这才是比较靠谱的,才能严防“化来化去”而不知所踪。举马克思主义的旗,首先需要有的就是马克思那样严谨的科学态度——起码的就是“实事求是”。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者就一直担心“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保·拉法格的信)看来,这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曾清晰地看见了“跳蚤”的横行并深受其害,故不能不警惕。█
(2016.2.27.发布/2018.10.24.修订)
〖前一页〗 1〖后一页〗
| 【相关链接】 |
||
|
||
| (本站 2018年10月24日发布 / 2020-06-04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