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教育理论/教育随笔>应学俊:改革高考——用好教育改革的“指挥棒” | | 您好!今天是: | |
 |
★ 本站时政评论目录
改革高考:用好教育改革的“指挥棒” |
| · 安 徽 / 应学俊 · |
(本文 2009 年获教育部、中国教育报联合颁二等奖) |
| 原创撰稿:应学俊(本站)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 2010年2月 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 |
【核心提示】 如果各省教育厅是可信的,如果各省教育厅主持有关学科的水平测试是可以做到科学、严格而有信度、效度的,全国统一时间的“高考”为何不能只考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基础学科?这三门课的高考成绩加上从省教育厅数据库中调取的考生以往相关学科水平测试的成绩,综合后,成为录取的成绩依据,有何不可? 本文将主要论述这一改革设想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高考改革构想。 【笔者2014年注】欣闻:本文所论在2014年全国高考改革方案中已有较多体现——在改革招生录取制度方面,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语数外的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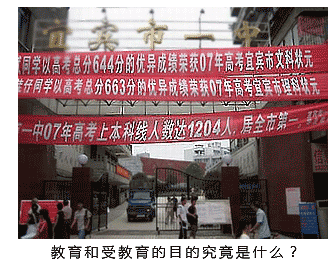 中国教育改革似乎比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难。改来改去,总在原地转着圈儿。素质教育从 1999 年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做出决定,要求“推进”,但 10年过去了(长于 8 年抗战),就是推而不进;而实际存在的“应试教育”却僵而不死,可谓阴魂不散,闻闻很臭,吃起来挺香。每年都有高中生因不堪压力而自戕的惨剧发生!何故?
中国教育改革似乎比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难。改来改去,总在原地转着圈儿。素质教育从 1999 年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做出决定,要求“推进”,但 10年过去了(长于 8 年抗战),就是推而不进;而实际存在的“应试教育”却僵而不死,可谓阴魂不散,闻闻很臭,吃起来挺香。每年都有高中生因不堪压力而自戕的惨剧发生!何故?
笔者曾撰文《用人唯学历——素质教育的“死结”》,从社会人才观及用人机制分析了个中缘由,《中国教育报》曾摘要刊发该文。但那是从宏观角度而论。具体到教育本身和系统内部,笔者认为,正是因为高考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无法推进。
“考试”——既是教育测量,也是教育评价的手段之一;对教育,它无疑具有“导向、激励”功能——亦即教育“指挥棒”的功能。中国“高考”无疑正是中国基础教育无形的“指挥棒”,它导引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牵动着全社会。下一万份文件,做一千场报告,不如高考的内容、形式立竿见影。这是无须论证的事实。
教育改革举步维艰,高考对教育客观存在的“指挥棒”作用又如此之灵,威力如此巨大,我们为何不运用这根“指挥棒”来促进教育改革?
高考改革改什么?怎样改才会真正有利于教育改革?笔者从教一辈子,研究教育一辈子,体会颇深。看法对不对,说出来供关心教育的朋友和决策者参考。当然,笔者所说也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和理念,如实施,其操作细节当然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减轻学生负担,高考只考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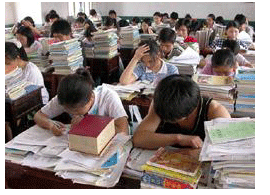 中国不少高中生戏称自己过的是解放前“包身工”的日子: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一直苦学到夜晚十一二点乃至更晚,每天大约只能睡四个小时,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究其原因,除了高考的残酷竞争以外,考试学科门数多是重要因素。
中国不少高中生戏称自己过的是解放前“包身工”的日子: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一直苦学到夜晚十一二点乃至更晚,每天大约只能睡四个小时,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究其原因,除了高考的残酷竞争以外,考试学科门数多是重要因素。
如果全国统一时间和内容的选拔性高考,只考语文、数学、外语,如何?笔者以为是可行的。发达国家如此做法的也不少。
这并不是说政、史、地、理、化、生不重要,更不是说可以偏废,而是不放在全国统一时间的高考中去考。一些地区中考的方法为什么不可以用?除了语、数、外,其它各科学完一门由全省统考(水平测试)一门,像高考一般严格组织命题、考试、阅卷,成绩由省教育厅统一管理(只要严格组织实施,各省统一测试的信度应当不亚于高考);高考录取时,以适当形式将存于各省教育厅数据库中该考生相关科目水平测试成绩记入该生总分。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各省教育厅组织学科水平测试和成绩集中入数据库管理的能力。
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向各省分配招生数指标,分数线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划定,有何不可?这难道不也相对体现了教育公平?
更重要的是,如此改革高考,从形式上未有大变动的情况下,却可以大大降低考生集中扎堆复习多门功课备考的压力,学生负担被分解了,同时也不会因为高考只考三门而导致学生不重视其它学科的学习。所谓文理该不该分科的事儿,也不必费心讨论了,学生的通识素质也将少一些“瘸腿”现象。
而由此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全国统一高考学科门数少了,考试、命题人力更加集中,时间更加宽裕,可以大大改变高考阅卷“草菅人命”的现象。中国人口众多,在历年高考中,阅卷教师时间紧、任务重,颇像大跃进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样各小组比着赶任务,十几秒、几十秒判一篇作文是常有的事情,可如此“草菅人命”怎么对得起汗流浃背拼搏数年的莘莘学子?公平公正和判卷的科学性如何保障?
二、转变教育观念,适当降低教材难度,改革考试命题和判卷方法
先说说“考试”与“减负”的关系问题。年年喊“减负”,可学生负担为何就是减不下来?除了因高考竞争、考试学科多,也与考试命题、方法密切相关。
在我国中小学教学中,学生需要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东西太多,这方面文科自然尤甚。新华书店里,所谓“教辅用书”几乎占去了书店半壁江山;其实,那实在就是压在学生身上的大山,其中有很多纯属重复训练和机械记忆,还有离奇古怪的各种试题。而我们的高考乃至各级考试,往往也较多偏重机械记忆的东西,据说这是“降低难度”之举。
从学与用的关系来看,从教育探索的实践经验而论——任何一门考试一般都应有这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对必须记忆、掌握的知识的考查,它应当与平时的教学要求相对应;二是对于灵活运用知识之能力的考查;三是对于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考查。而后两项考查,就高中而言,在分数权重上一般应当不低于70或60%。
一种值得借鉴的考试方法。在各科教学中,必然有须“死记硬背”的知识,但它应当是精选的,不是非常多的;越往高年级,需要死记硬背的相对越少。
笔者曾看到过这样的资料:有一些国家在高中或某些水平测试中,将答卷可能要用到而无须死记硬背的事实性知识、某些不常用到的公式、定理,以超过答卷所需的内容范围印发给考生,供其答卷时参考。窃以为,这是很值得借鉴且很科学的考试方法。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它将学生、教师的注意力引向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方面,而不是引向死记硬背可以查找到的事实性知识或不常用的知识方面。这样的考试方法就与陶行知“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谋而合了。在如此高考指挥棒的导引下,何愁中小学教学方法不随之改革?
应始终不忘“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禁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他曾经说:“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然,便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了。”陶行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阐述了教、学、做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某些基础知识的运用,我们在实践中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以律师为例,熟记法律条款应当是必须的吧?可有多少律师是能够“背”出整部法律、法规,乃至几十部几百部法律、法规的呢?
以政治、历史、地理老师为例,除了记忆力特好的,有多少老师能够不看书而说清楚他人随意指定的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具体过程及“评价要点”而毫错、漏呢?
多年做研究的学者、专家们可能熟记的内容多一些,而且如范曾那样能让众多古典诗词乃至《离骚》烂熟于胸的毕竟也不是很多。大多数学者做学问,每到具体引用某理论、材料时也未必不需要进图书馆或上网络查找资料(他们能大致记得基本大意和精髓,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原文),否则,学者家里要放那么大的书橱作甚?否则,他们为何要做许多的资料索引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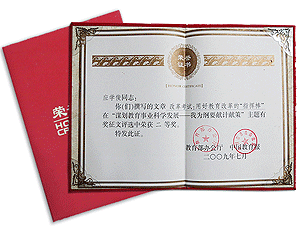 以上便是实践中“做”的具体情境,那些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大体能记得(背)一些最基本、最经典的内容,而对其它内容由于认真看过、理解过,所以大体记得在什么书、什么章节中会有,需要用的时候再去查找、验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做的法子”来指导学生“学的法子”和“考”的法子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将答卷可能要用到而无须死记硬背的事实性知识、不常用到的公式、定理,以超过答卷所需的内容范围印发给考生,从而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培养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以上便是实践中“做”的具体情境,那些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大体能记得(背)一些最基本、最经典的内容,而对其它内容由于认真看过、理解过,所以大体记得在什么书、什么章节中会有,需要用的时候再去查找、验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样“做的法子”来指导学生“学的法子”和“考”的法子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将答卷可能要用到而无须死记硬背的事实性知识、不常用到的公式、定理,以超过答卷所需的内容范围印发给考生,从而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培养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10-02 编辑发布 / 2018-04-05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