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反右专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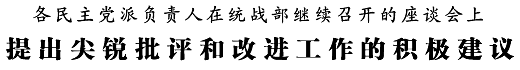 |
| 撰稿:人民日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 人次)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 (鼠标置于小标题处,可见相关介绍) | |
刘清扬,女,(1894-1977),中共早期党员,曾为探求救国之道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成立中共巴黎党小组,在留法中国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清扬因故失去了与中共组织联系以致最终脱党,但仍为妇女运动和中国革命不懈奔波。 1949年后,刘清扬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1961年,经多次要求,重新入党。对党可谓忠贞不渝。 “反右”中刘清扬侥幸逃过一劫,未打成“右派”。但到了“文革”她还是在劫难逃——1968年被捕入狱;1975年释放,坐共产党的牢房7年;1977年病逝于北京。文革终结后,中央为她彻底平反。 |
※ 刘清扬说: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建议,希望统战工作不要统男不统女 |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梅龚彬(1901-1975)中共情报史上的杰出人物,抗战三杰中的隐杰。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梅龚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眼里,梅龚彬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民主派;而在共产党眼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外),梅龚彬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 梅龚彬为人敦厚,深沉,诙谐,对朋友从无疾言厉色。做事谨慎,行侠仗义,古道热肠,见义勇为,肯帮衬,善守秘密,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种。 1932年起,梅龚彬表面上是大学教授,作家(灰色文化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福建事变,有军中“小孟尝”之称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广罗人才,梅龚彬和陈希周等中共党员受潘汉年派遣,入幕陈铭枢。1934年,闽变失败,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随十九路军撤香港,做长期卧底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 1947年梅龚彬又受潘汉年指派,到香港协助李济深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不久,民革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民革已在共产党掌握之中。 建国后,梅龚彬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中共党员梅龚彬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秘书长……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未公开。 1955年潘汉年冤案(毛钦定),梅龚斌受一定株连。 梅龚彬因其身份特殊,1957年未被打成“右派”。但1959年被隔离审查,后被劳改,过了8年共产党的铁窗生涯。 文革中,1975年5月,被专案组把正住院的梅龚彬强行带走送往江西宜春劳改。8月1日积郁而逝,终年75岁。 文革终结,梅龚彬获彻底平反。他的一些老友在悼念他时才如梦方醒——原来梅龚彬一直是中共党员,而非民主人士!纷纷感到惊愕和不可思议。 |
※ 梅龚彬说:在人事安排上 要使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1889-1973),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9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大学院(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暨联大、清华政治学系主任。1949年后,张奚若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在这次发言中关于“好大喜功……”的说法,虽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据李维汉回忆说: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本站评:呜呼,划不划“右派”,无须任何法律和程序,圣上一句话的事儿!】 毛一句话使他幸免“右派”,此外周恩来也力保了他;但张奚若还是在《人民日报》被点名批判。 而章伯钧、储安平等更多的人就没有张奚若的幸运了,参加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的民主人士相当多人后来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在他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明确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文革”时期,张奚若再度被周恩来列入12位应予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因此少受了许多冲击。故张奚若被一些人称为难得的“不死鸟”。(详见左侧相关链接) |
※ 张奚若发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
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
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
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16日继续举行。□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本站2009年11月转帖 最后更新:2018.02.06.
【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附录】毛泽东“诚邀”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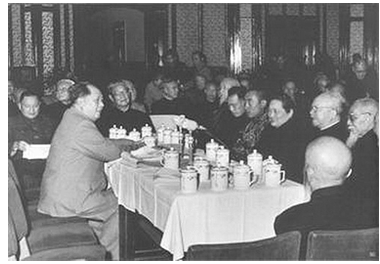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单位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单位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在这样诚恳的邀请下,5月出现了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高潮,大家提出许多改善党的领导、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中肯的建议。
5月4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向党内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诉省、部一级的党组织,“……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还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就是说要大家对共产党缺点错误进行批评,而不是评功摆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总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样的套话。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从5月初起,分别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召开了13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座谈会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中共的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消除了顾虑,鼓起了勇气,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辞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在这样的情势下,与会者都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每天报纸、电台都报导各界民主人士的发言。
对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央表示衷心欢迎并非常重视。在多次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对于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是大有益处的。在这些指示中,还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说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重视和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希望通过整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政府和各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然而,5月16日发言完毕,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座谈会休息几天。(实际上毛起草的有关“反击右派”的指示已经内部下发)
为何休会呢?当然是出了大事。多年之后李维汉在他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透露出来这个秘密。他说每次座谈会后他都向中央常委汇报,毛泽东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带有刺激的话,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之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很不满意,就决定要整这批人,并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
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让党内高级干部看,把这批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表明要反击右派的决心。这就是毛泽东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毛泽东还得意地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在诚邀他人提意见帮助整风的前提下,面对某些批评言论,而并非实质性对抗行为,采取“诱敌深入”的敌对性的打击——如何评价这样的行为?各人自有判断力)。
其后,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上一篇】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15.)
【下一篇】 章伯钧: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
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官方大事记)
| 点击右图返回: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 “整风-反右”历史记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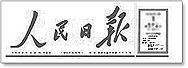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09-11 编辑转发 / 2018-02-06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