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 页>重读历史>“文革”研究>纪念遇罗克专辑>“血统论”的首创者与它的批判者殊途同归:蹲监狱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为坚持一个简单真理而牺牲的 |
||
重读历史
 |
历史钩沉
时评杂谈
“血统论”的首创者与它的批判者 |
| (本文原题《回忆遇罗克以及〈晚霞消失的时候〉》) |
作者:王斌、礼平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广州)/网易转载等 本站编辑转载(2010.01.12.) |
【原提要】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本文原发于2009年7月9日《南方周末》) 【本站注】后来人们误以为鼓吹上述“血统论”对联的原创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现名谭斌),其实这是大误会。谭力夫是因其1966年8月20日进一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首创者为何与它的批判者遇罗克“殊途同归”——蹲了监狱? 原因大致是:秦晓、孔丹、刘辉煊等“红二代”在文革狂飙突起几个月后,发现似乎不对头,觉得某些红卫兵一些过于暴力的胡抓乱斗老革命甚至随便打死人的做法应纠正(而且他们的父辈们基本都遭揪斗甚至抄家,成了“走资派”),他们认为这不会是毛搞“文革”的目的和用意,于是便模仿先辈“革命”中的“工人纠察队”,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来“管”另一些红卫兵,制止这类现象。他们初期的做法,曾得到中央部分尚未被完全打倒的老首长的支持,即所谓“黑后台”。逐渐,“西纠”对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言行也有所怀疑,认为毛恐怕被这些人糊弄了,对中央文革多有议论和“不敬”。中央文革很快嗅出了“西纠”的异常气息。后经毛同意,“五一六”、“西纠”、“联动”等这类从不同角度“干扰毛战略部署”和“怀疑、批判中央文革”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如此,他们这些“老子英雄”的“好汉”儿子们便被抓进了监狱。秦晓、刘辉煊等竟曾与遇罗克关在一处——可谓“殊途同归”。 当然,几年后秦晓、孔丹、刘辉煊等“红二代”也都上山下乡了,“反动组织”一事不了了之。到“文革”后,他们因其“红色基因”自然依旧是“好汉”,否则,他们何以大多成了大型国企、央企一把手?(也有成为学者的)。 其实逻辑很简单,谁妨碍了毛的“文革”,或对“文革”及“中央文革”有所怀疑,不管“红几代”,也是绝对不行的——连陶铸这样被毛调到中央文革的“忠臣”,对毛及中央文革的方针稍有懈怠或不同看法,都照样“全国共讨之”直至迫害致死——何况几个“红二代”?但对他们的最终处置自然还是网开一面的。遇罗克、张志新等等被枪杀,但“五一六”“西纠”“联动”这些所谓“反动组织”成员,在文革夺权结束后,毛亲自下令放掉(见《毛泽东文稿》),此“案”不了了之。怎样的逻辑还不清楚吗? |
 |
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遇罗克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
遇罗克之死的一般解读: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日学习,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80 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1979年11月21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王斌:今天回望1980 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 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
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 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
礼平:其实你关心的是我的经历:这个礼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他真的抄了人家的家了?(笑)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开头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革”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今天还在。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王斌:他们都是你们红卫兵的头头吧?
礼平:可以这么说。但那时他们可全都是反对红卫兵的。
王斌:那时反对红卫兵会冒很大的风险。
礼平: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
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
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像上官婉儿、冬妮娅,还有苔丝,等等,让人生怜。而这回我亲眼见到了,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
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至于这个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唐双津和这家旧军人的孙女之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至少是认识的。因为唐双津参军后,于1975年牺牲在了一次作战中。第二年,我写了这部小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王斌 礼平)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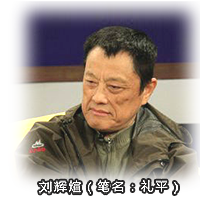 刘辉煊(笔名:礼平),1969年参军,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兵、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1980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论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离开了军队。回到北京后,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陆续发表中篇小说《走过群山》《小站的黄昏》《无风的山谷》《海龟的崖》及电影文学剧本《含风殿》。《无风的山谷》与《含风殿》获“昆仑”、“十月”杂志年度奖。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在鲁迅文学院退休。刘辉煊的父亲是老革命,但具体情况未见介绍。
刘辉煊(笔名:礼平),1969年参军,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兵、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1980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论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离开了军队。回到北京后,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陆续发表中篇小说《走过群山》《小站的黄昏》《无风的山谷》《海龟的崖》及电影文学剧本《含风殿》。《无风的山谷》与《含风殿》获“昆仑”、“十月”杂志年度奖。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在鲁迅文学院退休。刘辉煊的父亲是老革命,但具体情况未见介绍。 秦晓,“红二代、官二代”。文革前高三时,秦晓便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秦晓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据说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后在内蒙插队,“工农兵大学”时走入大学学堂。
秦晓,“红二代、官二代”。文革前高三时,秦晓便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秦晓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据说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后在内蒙插队,“工农兵大学”时走入大学学堂。1995年起,秦晓先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任院纪委第一书记;2001年至2010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
秦晓其父秦力生,是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文革”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文革”初期被夺权,受到冲击。文革后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后兼纪委第一书记。
 孔丹,“文革”前夕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高三,北京四中)。文革初,孔丹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对初期的“文革”运动有过很大影响。因孔丹及“西纠”涉“干扰毛文革战略部署、怀疑和反对中央文革”,孔曾两度入狱。
孔丹,“文革”前夕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高三,北京四中)。文革初,孔丹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对初期的“文革”运动有过很大影响。因孔丹及“西纠”涉“干扰毛文革战略部署、怀疑和反对中央文革”,孔曾两度入狱。
1968年底,孔丹上山下乡,落户陕北延长。1972年回京,1975年在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后直接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毕业后,曾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
孔丹其父孔原,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等职,母亲许明为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初父母被江青点名为“西纠黑后台”,父亲被关押多年、母亲1966年自杀。
在北京四中同学会上,红二代聚会,争论“宪政”问题。
原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先是质问招商局集团及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宪政?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还有没有信仰?”
秦晓则质问孔丹:“百姓的呼声你们就听不见,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
孔丹恼羞成怒:我cao你妈!(据孔丹后来对媒体说,分歧、争论是有的,但没爆粗口)。
有网友笑称:“孔丹同志送老婆孩子去美国是潜伏的,也为了他在大陆更好的革命工作,可是这么多人不理解,难怪他发火!”(孔丹妻儿实情在网上搜索不到,想必已向“组织”说清楚了吧。)
【编辑本文参考以下文献资料】
【相关阅读】
| 【延伸阅读】 |
||
|
||
| (本站 2019-01-01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