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 页>重读历史>文革研究>纪念张志新烈士专辑>【回忆】张志勤:触摸悲怆的音符(转载)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其它“重读历史”资讯:

点击:到“张志新专辑”…
【和着血泪的回忆】 |
|
她的姐姐曾经行走于历史的刀锋之间 死于黎明前的黑暗 留下了醒世的苍凉 |
张志勤:触摸悲怆的音符 |
| · 田子 · |
| 作者:田子(《英才》期刊记者) 来源:中国知网、百度学术等(1999年) 本站编辑转发 |
她的姐姐,曾行走于历史的刀锋之间,死于黎明前的黑暗,留下了醒世的苍凉。
张志新,是一个遥远又不太遥远的故事,曾有几代人同时知道了她。
1975 年4 月4 日,是张志新那个烈女子牺牲的日子。
今年,为她平反整整20 周年了,接近一位往昔英雄的足迹我以为很容易,然而我想错了。千辛万苦从沈阳打电话一路寻找,直到找到张志新的二妹张志惠,她声音发颤但坚决地一囗回绝。
我以为回忆是一种刺激,但再咬着牙打电话过去才得知,在我之前有一位写张志新“婚外恋”的某报记者曾以道歉为名采访过她,之后,违背自己的承诺,发表了“一篇变本加厉歪曲事实的文章”, 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一听“记者”便如惊弓之鸟。
但真诚是世界上沟通的最好方式,我以一百二十分的真诚赢得了她的信任,才有了这次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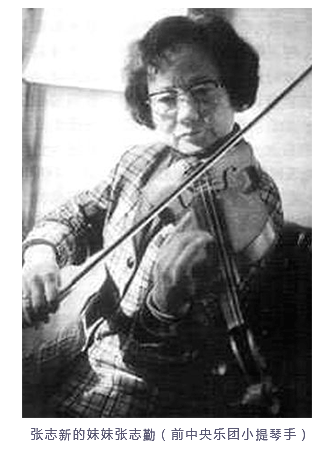 在一个大风天,我走进张志新的三妹张志勤家。面对姐姐志新的遗像,张志勤拉起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悲伤凄美的一段。好久,我们相对无言。后来我知道这是张志新前最喜欢听也最喜欢拉的小提琴曲。
在一个大风天,我走进张志新的三妹张志勤家。面对姐姐志新的遗像,张志勤拉起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悲伤凄美的一段。好久,我们相对无言。后来我知道这是张志新前最喜欢听也最喜欢拉的小提琴曲。
动笔之前是段艰难过程,主要是我自己不能平静自己,理智地下笔。
§ 亲情与真情
张氏三姐妹在天津音乐界曾是颇有名气的才女,常随父亲出演音乐会,每次都少不了“弦乐三重奏”。三姐妹,大姐是志新、二妹志惠、三妹志勤。她们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叁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两人都从事教育工作。
张志勤清楚地记得,因家境实在不好,大姐志新10 岁以后才开始上学,直到中学都是一边帮妈妈干事,辅导妹妹们,一边读书。
张志勤说:“七八岁时,父亲发现我有音乐天赋,对我说你将来一定要当中国小提琴家。这个愿望一直固执地影响我。”“整个学生时代我只顾拉琴,政治上我只想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可不知为什么一有运动就挨批,总在改造。”曾师从马思聪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谭淑贞的张志勤,学生时代还是处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回忆起来,无奈就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姐姐的关怀更显得弥足珍贵。
 |
“我总想不通,姐姐当时在北京人大念书,常给我写信,出差也常来看我。她自己生活俭朴,还给我买了一条围巾,白底印着兰花,她希望我做人和心灵都能像这条围巾这么纯洁。这条围巾我一直没用,留到今天。
“我十七八岁时,因为要凑右派名额,就把我打成右倾分子,开会前要斗争我,我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最痛苦时想跳海河,一回家就哇哇大哭。大姐调沈阳前,到音乐学院了解我的情况,劝我,鼓励我,她知道我根本对付不了政治运动,特别容易被人陷害,她帮我写检查。告诉我一定要有政治头脑,不要随大流。”
志勤说,大姐1950 年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那段岁月可以说是她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亮丽得让人嫉妒,她是学校业余舞蹈队队长,最擅长跳英姿昂扬、节奏明快的蒙古舞,你可以想像那时漂亮的志新多么青春可爱。毕业后因工作需要她留在人民大学资料室搞翻译工作。如果不是后来随夫婿调到辽宁沈阳,她的命运或许是一片坦途。
张志勤对大姐在政治上超常见解记忆犹新。
“我两次到沈阳演出时都去看姐姐。她特关心国家大事,思想境界不只是限於生活小圈子。有一次地竟哭着说:大跃进极左到了虚报高产量,产不了那么多粮食,农民就把每个月很可怜的那点儿油往地里倒。我当时无法理解她为什么那么痛心。她真的是忧国忧民,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前途。”
可怕的政治环境,注定了志新这个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遭遇悲剧的必然性。
§ 诀别赠言
1968 年,也许是大姐看到了某种征兆,也许是她已做好准备为真理而献身了,亲自把女儿林林送到天津上学。“她本想把女儿一直留在天津,但看两个老人身体情况太差了,屋子也只有一间,而我又没成家,不能照顾林林,她又把林林接走了。”张志勤回忆道。
张志新这次到天津、北京省亲,也成张氏三姐妹最推心置腹、最长久、最难忘的一次会面。那天她们都聚在张志惠家,3 个人从晚上11 点一直聊到天亮。但她们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她们和大姐的最后一面。
像老天的安排,她在京滞留的极短时间内,每个兄妹家都去了,二哥、三哥都问候了。“文革中她一个一个地关心着我们,帮着我们。没想到,她自己被迫害时,连老天也无能为力。”张志勤的叙述中充满了一切刻骨的悲痛。
也许是自己婚姻的不尽人意,张志新才对自己的女儿和还未成婚的妹妹张志勤有了过多过早的考虑。她说:“女孩子小时不能总穿新衣服,打扮得特漂亮,这样她长大后就会只注意外表,会虚荣。一定要让她把精力用在学习上,经济上要独立,人格要过得硬。”
她劝三妹志勤找对象一要看人的品质,不管他是穷是富。他品质好,你一生都幸福。
§ 永远的悲痛
都说兄妹如手足,手足的十指都连心,突然一根手指被切去,永远痛的只有心。
“1968 年11月,姐姐写信嘱咐我要经常回天津看望父母,告诉我父母容易得什么病,该准备什么药。我哪里知道姐姐这是把老人嘱托给我,是准备义无反顾地捍卫她心中的真理。我更没想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得到她的来信,这封信也成了姐姐留给我的最后遗迹。”
1969 年9 月24 日,志新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经历了无法想像的折磨後,不屈的张志新于1975 年4月4日被残酷杀害。
张志勤获悉姐姐被害是突如其来的。“1976 年6 月的一天,辽宁曾经来做过外调的那个人又来了,我当时正怀着5个月的身孕。他说:‘张志新早就处决了!’我哗的一下全身只往下沉,赶快两手扶着凳子,强忍着眼泪和悲痛,半天才说,我姐犯了什么罪,到了枪毙的份上?‘现行反革命,不处决不足以平民愤。我们来是找她母亲处理遗物的’”。
“这沉重的打击,使我常常精神恍惚而自言自语。为不让在我家养病的母亲看破,也不让正在我家治病的姐姐的女儿林林知道,我每天强忍着眼泪,装着没事的样子。看着林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永远地失去了母亲,年迈的妈妈不知道牵肠挂肚的女儿终未幸免于难,每次一回到自己屋子里,我就暗暗落泪,心如刀割。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给姐夫曾真写信,没想到信在我上班时被母亲无意中看到。老人悲痛欲绝,三天没有起来,整天蒙着被子含悲啜泣,因为怕被人听见,不敢放声痛哭。我们都非常担忧,但第四天母亲却坐起来,没有眼泪,怒向东方,一字一句地说:‘别担心我,不看到给志新昭雪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
果然有冥冥中的力量,坚强的老妈妈真的等到了那一天,并亲自动笔为女儿赋诗一首。
 |
有人说世界上实际没有英雄,萨特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描述的几个人,在面对可能被敌人杀害时,并不是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恐惧,都想当今天所说的叛徒,最后他们都招了假供。但萨特如活在今天,他必须为他的论断留下别样的注脚——张志新至死没有当自己信念的“叛徒”!
人的第一意识是生存意识,生存意识压倒一切时,什么意念都枉然。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真的孤注一掷、死不回头时,应该说有什么曾让她深深失望、伤心,只是让她感到眼前的一切无比的丑恶和肮脏,以至彻底摧毁了她对人世的留恋。同时,也应有什么事曾让她的信念坚定过,这信念能压得过生存意识,让她觉得死得其所。
一生无媚骨,至死不认罪。该有几人能做到? □
(本文原发于《英才》刊物1999 年第7 期。本站转载有极个别字句修订。敬请原作者谅解)
【原文附记】
张志新身后留有一儿一女,彤彤和林林,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在国外工作。
她父母都已去世。三个兄长中,大哥去世,二哥、三哥都曾在北京教书,都已退休。二妹志惠也从人大附小退休。三妹志勤曾是中央乐团国家一级演员(小提琴演奏家)。最小的妹妹在美国定居。
在张志新牺牲10周年时,曾开过家庭音乐会,三姐妹中的二姐为九泉之下的姐姐演奏了《悲歌》、《谁之罪》等乐曲。张志勤说:“每年4月4日,我就要对着姐姐的遗像拉给她听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自言自语:姐姐,我来看你了,你听见了吗?我总觉得她有许多话还没有说完,我要能替她死该多好。”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05-04-05 编辑转发 / 2018-12-18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