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沉重的1957-1965>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历史纪实 /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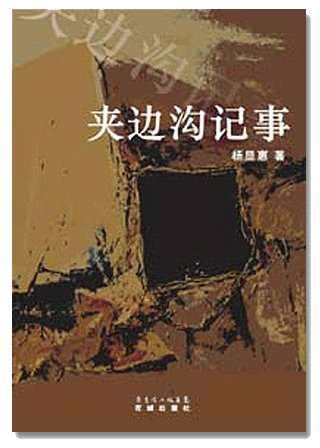
| 近 期 评 论 |
点击:更多评论
| · “反右运动”纪录与反思 · |
|
| 作者:戴晴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2003年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 点击标题浏览: |
1、帽 子 |
2、社会主义阵营 |
3、个人英雄主义 |
4、勉 强 |
5、谋 |
6、命 |
(续第1页)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那阵子推出的新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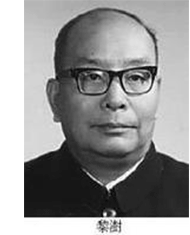 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 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的。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 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 1955 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牟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 |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支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支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札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繁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们的观望恰恰形成对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
从1956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做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
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狯,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维护党而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真是前所未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的解决充满信心。 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容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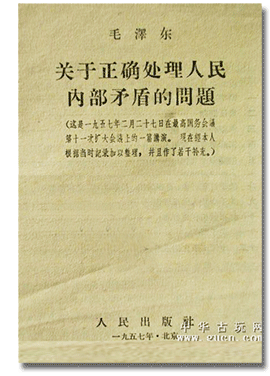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悖之处。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悖之处。
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性矛盾?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法则的语言要求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
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 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的欢愉与温暖。直到1957年9月19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本站注】关于此,沈志华教授的历史讲座《从“整风”到“反右”的演变过程》有基于史实的更透彻讲述和评析,可点击观看)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参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 年所闻所见本己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 年所闻所见本己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
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入“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1950年代未,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19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 15 天之后的语言——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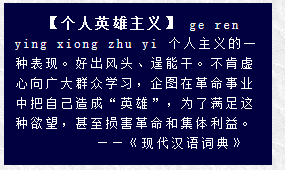 1909 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
1909 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
其实这两说都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储家或许可称作大富:在宜兴那种地方,他的祖父拥有上千亩土地。这老人有三个儿子,储安平的父亲排行老二,分家时得了300多亩田。这位先生开头可能相当热衷功名,曾北上做过一任不大不小的京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官做不下去,人也做不下去了。他开始花天酒地打发日子。储安平出生仅数月母亲即过世,抚养他的是祖母。当父亲续弦,旋即又出走去花天酒地时,少年储安平面对着的,只有那位带着一个小女儿,并怀着一腔幽怨的继母了。
“祖母过世以后,不知她们母女吃什么,我单独吃饭,一块腐乳吃三四天。过年过节给一点肉酱,也是一吃几天。”储安平对他妻子这样回忆过。
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17~19 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200 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这本出自少年人之手的小说集今天在北京图书馆被归为“蓝参”,即只有持有身分证明的读者方可阅读的一类书。
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 年到1932 年。这段时间,正是新月派的一批博学、散淡、且极具自由与浪漫气质的教授们集于上海,并活跃于课堂上与课堂下的时候。当然,按照新编《辞海》1980年版,新月派是“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字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储安平当时对此肯定无所察觉,他甚至很不像个新月派,因为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
在储安平数十万字的遗文中,没有一首诗。而这是每个中国文人,包括没有仗可打的将帅们,全部随大流顺手弄弄的玩意儿。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
留学成了他日夜索怀于心的梦——其热切程度恐怕不在今天数以十万计星夜排队等着取“托福”表格的青年之下。或许缘于凄凉的童年生活的阴影,他渴望出人头地,而不留学则绝无出头的一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的这一判断是多么背时,多么贻害于己。他不是衣食无虞的阔少,想留学,要靠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这愿望,直到他娶妻生子之后才实现——这是后话。
在大学里,他没有停止写作,但投稿的方向,已经由申报转向大公报。青春骚动期过去之后,他即不再写小说。大学尚未毕业,他关注的热点已转向政局。21 岁,他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薄薄的一册,约十多万字,收入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20 多位学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
拿到这份资料时,笔者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不在书法,储安平字写得如何从来不曾被人提起过。当然看见这几个字很难让你不想起今日北京大学学生虫子爬出般的大字报。
今天,35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60岁还属“中青年学者”,何为韶光、何为英年,恐怕常常出现在梦里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中吧!娇儿已经绕膝,习惯了的还是“接受”、“领会”和一切小字辈的唯唯——题辞作序是德高望重者的事,当然当官职大到老先生们在他进门时也不得不站起来笑着点头等候握手者也有,但在这般年纪而有如此气势与号召力的,在中国恐怕只有靠他令尊坐着的那把交椅了。今日大学生,就算已经不是21岁,而22、23、24岁,若想赚点零花钱,对不起,在校园里摆摊卖茶叶蛋吧。
请看这位1930年代学子的口气: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
这篇序写于10月,而11月书就出版了——这种速度今天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在朝要人”可享有——而徐志摩的遇难恰在那年11月。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由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接手,“致使它原有的文学艺术意味,几乎全为政治气氛所笼罩所淹没”。由此推测,这本书应是在罗隆基的主持下出版的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对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的这位“盟主”,储安平并未视为终生恩师——虽然他们的名字自1957 年就被绑到一起,直到今天。
毕业之后,储安平养病一年。以他经济之窘迫与求学心之迫切,这似乎有点费解,但也足见幼时营养缺乏之结果。储安平一生都不曾有过健康充沛的体质。他个子长大,或许因为用得太过,总是处于“透支”状态。以他撰写《英国采风录》为例,这本10万字的书,居然完成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他不安于作难民,“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竟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这样的用语是很奇特的,可见工作于他绝不是徐志摩式的“想飞”,也不是达尔文式的着迷,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约束。这很可能来自他少时乡居生活的清苦刻板,也许是对英国式的公道(hairplav)和直道(justice)的崇信,坚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气短,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取这种人生姿态,真使他吃够了苦头。他没有了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失去了人世间纯朴的亲情之爱,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sy ——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元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
他很快有了职业,在南京为《中央日报》编副刊。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权势背景、又非国民党党员的穷学生能谋到这份差事。考查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央日报在文化界太没面子,急需找人撑场,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凡有别的办法,是不肯到这种地方来的。作为第二代新月派才子,储安平的资格还说得过去,加之他又急于谋职……总之,他上任了,而且颇为得意。因为一般大学毕业生只能拿到60~80 元一个月,他则拿到120元。25岁的他,租了一所花园洋房,院子里能打高尔夫球,客厅可招待七八对跳舞。他开始结交权贵,请他们吃饭、陪他们打牌——他实际上很讨厌打牌,而且根本不会打,一夜就输掉一二百,而交给太太的菜金,却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编副刊的同时,他还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往来于曹禹、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
这时,已经很难想象,不过二年前,他还随着一批热血青年,准备北上投奔马占山,参加东北抗日!他们在北平被劝阻,并且就地入学了。所以,在储安平的学历中,还应有段燕大的学习生活。但他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sy 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柏林奥运会开幕。说起来真够可怜——中国那时穷得连记者都派不出。储安平捉住这个机会,提出不必拨专款,只须让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可完成报道。他那时已有了自己的一小笔钱,还由把积蓄全部花到家乡的善卷洞、张公洞的伯父出面,为他申请到江苏省的2000 元官费——这就是在1957 年屡屡被提到的“和国民党张道藩交往甚密,托张说项,得到教育厅补助”的那笔钱。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去了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
正是从那时起,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储安平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有。
储安平27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终身”。他没有组党,参加党派的时间非常后;在政界,无论当权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是重要的党派成员。他热烈地主张并为之鼓吹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用《辞海》的话说,是“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可以想象,这种反对,无论从1928到1948,还是1949到1968——这正是储安平从19岁到57 岁的近40年间——总是令当权者(特别当这当权者又颇具专制倾向时)恼火的,所以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几乎从国共双方所编的史书中消失了。他们的为后人所识,只为他们的个人身分:哲学家、律师、记者等等,而他们的政治主张简直就如一茎小海草,完全淹没在中国农民意识的大洋之中。
1938年,储安平归国,在英国耽了不足4年。这期间,他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只具名义,不支薪水,但发回来的稿,发表后所得稿酬,则由中央日报兑成英镑汇去。可能因为学业太重,也可能顾忌派驻记者的身分,储安平没有打工。开源之路既绝,只有节流一法。据他自己描述:“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留学生,但至少可以列入第一等的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4镑,合当时国币约为65元左右,而庚款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24磅。”他如何节衣缩食呢——“那时,因脚爪之价格较猪肉为廉,日日吃猪脚爪烧白菜”,因“脚爪无甚营养价值,久吃之后,健康不支,才改食干酪”。
Lusy第二年也去了。两个南京生的儿子,一个3岁,一个1岁,丢给了外祖母和祖母。除了中央日报,他还想方设法给别家投稿,这也颇不易。直到1957年,“章罗联盟”一说提出,在交待与该盟的关系时,他在英国的这段东拼西凑的日子才得以披露:
大约在1937年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3年稿费才到英国读书的。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 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
抗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学业未卒,即提前回来了。当时,《大公报》曾有延聘之意,储问能不能任主笔,因为那时中央日报是请他以这一资格出台的。未能遂愿,经比较他还是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
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掉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一年之后,这研究员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照张的意思,若续聘,必须同时接下两份聘书,一为研究员,另一份是一纸国民党特别党员(即无候补期者)的入党志愿书,他回绝了。
不能说他在那时对国民党就已经有了写《一场烂污》时的认识;也不能说他对官场已全面憎恶——直到1948年,他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老同学如沈昌焕等依旧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但他不愿侧身其中。他的直觉是:“没意思,还是超然一点好。”
就在这时,老教育家、原光华副校长廖世承出面,在湘西组建国立兰田师范学院。不少光华同学都出任教席,储安平带着妻子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也去了。
这时已是1941年。储安平那年32 岁。
不知他当初在伦敦读政治系时有没有从仕的打算,就算有,在他回来3年之后,在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面前恐怕已经绝了望。在兰田,他终于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使他的见解得以以作学问的方式无拘束地发挥。他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给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英国宪法。据Lusy回忆,每逢周会,教授们是要轮流演讲的,轮到安平,“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他在这里赢得了学生与校方两方面的赏识。
后来为办《观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力劝父亲卖了地作开办金的雷柏龄,就是当年的学生。储安平务实的精神与经营的才干此时已略见端倪:在那动乱的年月,而且是湘西那种地方,他居然编起一套丛书,共10册,自印自装自办发行,销路还颇好。而卖书所得,他不购置田地,不存黄货,却买成成匹的布,由学生挑进挑出。
最不争气的依然是他的身体。虽然他已尽环境与财力的可能,吃饱吃好,依旧十分羸弱。校长曾在过年时,专门送他一笔慰问金,以滋补身体。不知这是否就是1957 年批判时屡屡提到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汇寄的一笔医药补助费”。
抗战胜利之后,学校内迁,他回到重庆。
1945~1946 年的重庆,真是热闹非凡。如果不考虑沪宁杭、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军队的频繁调动与冲突,在重庆的这一方舞台上,真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体系、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平等与平心静气的大交锋。当然这平等仅指人格与观念而言。尽管这样,令后辈学人感到欣喜的是,毕竟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子弹而靠理性与才智而发言。
上面提到过的五名“不予改正右派”中的三名,此刻正混迹其间:
章伯钧,1928年脱党的原中共党员、闽变的参加者、民盟与农工民主党领袖。那时,他正以参政员的身分飞延安商谈国事,并作为党派代表出席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老政协)。
罗隆基,著名英美派教授,国家社会党创始人、民盟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届时与中共合作亲密。当中共代表团愤然撤离重庆时,他曾与王若飞紧紧拥抱,热情洋溢地保证:“放心,一定努力干下去!”
和前两位比,储安平无论年龄还是资格都稍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场与做法。
储安平当时在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这是一份闲差,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他那时候刚遭婚变,正照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这阶段,他没有结交任何一位共产党人,也没参加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与此相反的是邓初民——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他们一批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费边社信徒,正幻想着持枪的双方能平心静气地一道坐下来讨论中国的民主政体。他和梁漱溟的友谊想来就是此时开始的。虽然梁先生是实实在在地厕身其间,而安平仅仅站在一边评头品足。
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这很像是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编。
1946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 OBSERVER 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1946年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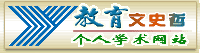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站长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