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1957-1965>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转载) - P.3.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点击这里展开:关于“大跃进”
“大跃进”:是指1958 年至1960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无视客观规律,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对不同意见一概以“右倾”“右派”予以打压,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在工业上,典型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则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似乎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了。而这两个历时约3年的“运动”,使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挫折,并直接导致波及全国的打饥荒。 除所谓“反右派斗争”55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群众因为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和打击,上至省长,下至普通群众。 上有好者,下必趋之。在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氛围中,违背规律的“大跃进”终于导致经济滑坡和波及全国的大饥荒…… 如果说工业上的“大跃进”后来有了明显有效的纠正,而“人民公社”则只纠正了一些“共产”过激的因素,一直维持到毛去世及改革开放,才彻底终结。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相关资料/视频
重读历史——

| ·高王凌· |
| 作者:高王凌 来源:原载“中国新闻周刊”/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2004年已发布 本站编辑转发 |
| (点击这里到:上篇:大跃进时期) |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主要集中于1959—1961年,包括“继续跃进”、“三年困难”,以及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战争”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使用了除起义造反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它使这一反抗带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也显得格外正义和悲壮。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描述出这三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大饥荒的情况),资料的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从本项研究的主题出发,最重要的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努力探索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反应,哪怕它仍不够全面。
在前一个部分我们曾强调 1958 年的特殊意义,确实,由于“纠偏”的存在,“大跃进”这几年的历史似乎被割断了。但在读过本章之后,不难看出, 1958 年和 1959—1961 年这两个时期,其实还是一段历史。
如同前一部分,本文首先叙述这一段历史的简要过程和主要事件,然后再依次讨论农村情况和农民反应。
一、继续跃进和三年困难
1)庐山会议和“反右倾”
 1958年,共产党企图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向“理想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则是为经济上的“大跃进”服务。这种组织以“公有”为原则,以行政命令之下人员和物资的集中使用和无偿调拨为方式,以尽量缩小乃至铲除个人权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底里,因而立即演化为“抢产共产”,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纠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8年,共产党企图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向“理想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则是为经济上的“大跃进”服务。这种组织以“公有”为原则,以行政命令之下人员和物资的集中使用和无偿调拨为方式,以尽量缩小乃至铲除个人权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底里,因而立即演化为“抢产共产”,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纠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纠偏的目的是纠正偏向,以利再战,并不是要取消“大跃进”。因此,到1959年年中,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后退”,(1) 随后在庐山召开会议,准备由批“左”转为赶快抓 1959 年的“跃进”。(2)
“纠偏”只是承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偏向,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例如对“共产风”的纠正,实际上远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彻底,若干省份连中央的有关指示都没有传达,甚至把它认作“反面材料”;(3) 对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以为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因此说会前走了四省,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4)
因此无论如何,庐山会议都不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5) 正是有鉴于会议不能正视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严重的问题,彭德怀写了给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导致了“反右倾”的出现。(本站注:庐山会议原本是想适当纠左的,是给人发发牢骚提提建议的“神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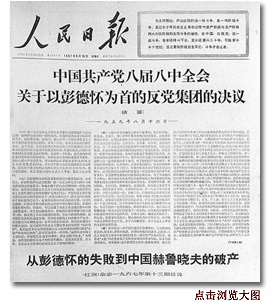 彭德怀的信讲出了许多实际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很尖锐的。其目的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6) 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做了对他的冒犯,是动摇三面红旗,有损于他的权威和革命理想的实施。(7) 其实在彭的信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写到,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全国春播较1957年减少 9000 万亩,以及市场紧张……等等。(8) 这些绝不是什么“鸡毛蒜皮”或“一个指头”的问题,由此可知,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的争论的发生,确是迟早难以避免的。(9)
彭德怀的信讲出了许多实际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很尖锐的。其目的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6) 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做了对他的冒犯,是动摇三面红旗,有损于他的权威和革命理想的实施。(7) 其实在彭的信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写到,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全国春播较1957年减少 9000 万亩,以及市场紧张……等等。(8) 这些绝不是什么“鸡毛蒜皮”或“一个指头”的问题,由此可知,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的争论的发生,确是迟早难以避免的。(9)
【本站补充视频资料:1959 年纪事之三:“神仙会”上风云突变(彭德怀蒙冤)![]() 】
】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中,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批判和受到组织处分。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如果把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也包括在内,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远远超出了“右派”的人数)。这些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提出批评意见的人。(10)
【本站补充资料:1、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2、图文网页: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之蒙冤往事】
2)继续“跃进”(大跃进的第二回合)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重新吹响了“跃进”的号角。彭德怀在当年的笔记中曾写道∶“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事情的发展竟完全证实了他的忧虑。(11)
继续“跃进”首先表现在高指标上,其中尤以钢铁“一马当先”,其次则是粮食、煤炭等。钢,在1958年仅生产了800万吨,为北戴河会议确定指标的75%。拟定1959年计划时,钢由3000万吨的高起点,逐步压缩,减至1800万吨,4月调至1650万,5月压到1300万吨。实际产量达到1387万吨。
1960 年的计划,由于受到“反右倾”的影响,许多人头脑再度发热,指标无法调整,由庐山会议的1840万吨,到1960年初,修改为三本帐,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要求确保完成第二本帐,争取实现第三本帐。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造成经济生活的更大危机。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计划生产钢2010万吨,1961年6月调低到1100万吨(估计至多能完成850万吨)。所以说三年大炼钢铁,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重工业的“单兵突进”,使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12)
粮食,原公布1958年产量7500亿斤,庐山会议修改为5000亿斤;1959年指标也由10500亿斤,调为5500亿斤,当年实际产粮3400亿斤(虚报为5400亿斤)。1960年指标,庐山会议确定为6500亿斤,以后减至6000亿斤,实际产粮仅2870亿斤。1961年计划产粮3900亿斤,后调高为4100亿斤,当时预计只能生产2700亿斤。(13)
尽管到1960年中央同意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但直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西楼会议”下了退够的决心之后,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方落到了实处。(14)
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从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至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利害。(15)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发生“共产风”的主要契机,如果说是“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三级所有体制后还继续刮“共产风”,主要契机则是急于过渡。因为它没有改变原有三四年、五六年或更多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观点,而且强调“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壮大社一级经济。所以会后不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少地方就开始制定过渡的规划。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提出了限期(八年)过渡的要求。会后各省开始试点,有的要求“六零年试办,六一年大办,六二年渡完”,并产生迟早要过渡,因此“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以及平调“没有什么”的思想。(16)
据1961年8月统计,几年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乡村人口计,平均每人49元(1961年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仅为68元)。(17)
1960年11月中央指示彻底纠正“五风”,在所附湖北省有关报告中指出,“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据湖南某地统计,如果以三年来平调这个公社农民的财富总额为100,则各时期所占的比重是∶公社成立前为 6%,公社建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前为48%,1959年其余时间为20%,1960年为26%,也就是庐山会议以后约占平调总量一半。(18)
事后毛泽东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反右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19)
3)三年困难
正如“大跃进”在时间上是指 1958—1960 年,“三年困难”主要是指 1959—1961 年,但它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从一般认识来说,它主要是指农产品的提供和人民生活这一方面而言。
从 1959 年始,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例如粮食产量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 2.5% (当时以为有7500亿斤);1959年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为2870亿斤,年平均递减15%,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1961年有所回升,产粮2950亿斤。(20) 在1960年,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回到1951年即建国初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1951年的一半)。在主要农产品严重减产的同时,征购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8年为1175亿斤,1959年1348亿斤,1960年1021亿斤,分别占总产量的29%、40%和36%。粮食库存量,到1960年末降至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29%。出现了严重的全国性的粮食危机。(21)
大跃进的损失,又不仅在于农业和粮食,而是及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轻工业生产的下降,以及山林大破坏等等,据统计,大跃进期间的损失共约1200亿元,人均近200元。(22)
造成生产严重下降的原因,在农业方面,据说主要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没有心思生产,生产力遭到破坏,劳力外流,农具损坏,疾病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例如,1958年秋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11000万亩);1959年约有30%的春播地缺少底肥,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7400万亩;1960年比去年少播冬小麦8300万亩,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板茬下种和未施底肥,或下种量偏低和下种失期。至于1959—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55200万亩)等,与各种人为因素相比,只能说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23) (【补充-本站编辑】当今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述和评)
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1957年比较,1958-1960年分别增加了197亿斤、342亿斤和61亿斤;而农业销售量增加很少,它们分别增加51、104和103亿斤。农村粮食的输出量,分别为708、799和520亿斤;与1957年比较,1958和1959年分别增加147和238亿,1960年减少42亿斤。
粮食进出口,1958—1960 年分别出口 65、95、20 亿斤,较前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直到1961年才开始进口(94亿斤)。粮食库存,1958—1959年基本持平(略低于1957年水平),所谓挖库存若干,皆因出口所致;1960年挖库存较多(176亿斤),主要用于国内需要(以上皆为贸易粮)。(24)
在三年困难以前的5年,全国乡村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为 396 斤(不计自留地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59—1961年依次下降为366、312和308斤,平均330斤,减少了17%,因为取消了自留地,农民口粮实际下降的幅度较之更大。如以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人均年度口粮减少了182斤。(25) 上述情况,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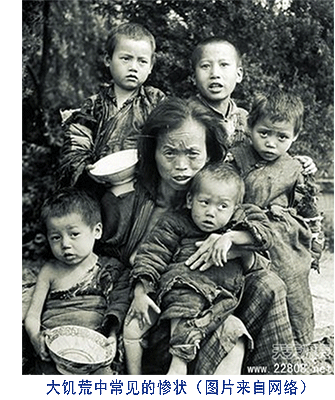 根据现有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 2.22% ,已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1961年为65859万,累计减少135万人。不过,以上这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据《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减少实际比 1000 万还要多(也不可能是整整减少1000万人);1961年人口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三年累计减少数则为 1486 万人。如果考虑进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26) 另据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统计,1961年比之1957年,农业劳力即减少了2000万个。(27) 【本站补充视频资料:林蕴晖教授主讲:三年“困难时期”
根据现有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 2.22% ,已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1961年为65859万,累计减少135万人。不过,以上这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据《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减少实际比 1000 万还要多(也不可能是整整减少1000万人);1961年人口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三年累计减少数则为 1486 万人。如果考虑进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26) 另据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统计,1961年比之1957年,农业劳力即减少了2000万个。(27) 【本站补充视频资料:林蕴晖教授主讲:三年“困难时期” ![]() 】
】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了。
如前所述,1959年初发生了严重的春荒。据说,1959年初河南豫东五县及开封地区已饿死数万人。(28)
4月,毛泽东批转了名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文件。不久又了解到,河南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河北春荒停止发展,但还未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山东农民外流已经停止,浮肿病开始下降,一些地区春荒还在发展。(29) 这时,许多省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比较严重,广东、山东有的地方还发现了抢粮事件。(30) 随即在若干地区发生了夏荒。
到7月份,全国 6 个月的存粮只有 310 亿斤。(31)
但是在庐山会议上,粮食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毛泽东文稿》中看,会后也不再见有类似的反映(而只有“跃进”的报告)。(32) 事后,毛泽东说,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33) 但到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这个冬天,可能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个时期。【本站补充:请参阅人民网载文:《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图)》 | 另一链接】
二、农村境况和农民反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最突出的就是粮食和“共产风”问题。
庐山会议以后,“共产风”不但没有制止,比 1958 年刮得还利害。1960年初广东发现,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错误;山东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类似的问题,各地都有,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34) 10 月指出,这一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两年以来,“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到工作队进村,有的队还在收自留地。刮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基层,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无所不刮。其中仅刮个人的,就有农具35000件,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0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或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
公社化以来,某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刮了19次。经粗略计算,每人平均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元,相当于一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上的瞎指挥,也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一刀切”统一指挥的办法,全公社统一行动,要干什么都干什么。在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队把种子都卖光了。(35)
在其后发出的材料中说,沔阳县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省、县、社、队四级,共圈占土地30000亩,占用社员房屋4400 栋,拆毁房屋 8200 栋,刮大中小农具84900件,各种家具170000件,砖瓦1887万块,调骡马700多头,生猪17900头,粮食119万斤,其中无物可兑部分,共折款276万元。(36)
报告指出,刮共产风、瞎指挥、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作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提高工效和细收细打?结果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与1957或1958年比较,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37)
由此可见,“共产风”不仅是为了抢先过渡,也是发展社有企业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成为一个现实的考虑,否则社有企业就不能“无中生有”,有了也不可能充实。简言之,不“共产”,人力物力资源从哪里来?大办快上如何办到?“优越性”又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公社体制“好管理好领导”的必然产物,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对这样一套体制,恐怕不能称为什么“工业方式”,而毋宁说是“官僚式”、“极权式”和“军营式”的。因此要想反掉“共产风”,就不能不痛下决心。这才有了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连续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从此以后,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才得以制止,但它在中国大陆上反复蹂躏,已有两年之久了。
在山西太谷,“共产风”相当严重,从1958年5月以来,大风刮过两次(1958年秋公社化后,1959年反右倾整风后),小风不断,边纠边刮,纠了又刮,几乎每一个运动,每一项工作,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在不同的刮共产风。最主要的有十个方面:
1)1958年春季大搞水利,夏季植树造林,无偿调动劳力,并发动干部、社员投资水利建设公债。
2)大搞电气化,积资献宝运动,计有金、银、铜、铁、锡、珠宝、玉器、药、砖瓦木料石、箱、柜、棉布等,无所不包。
3)公社化后,搞食堂、“五化”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有的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有的实行“天下人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有的实行“十大”包干、“八大”包干的供给制,有的实行男女老少分住分吃,说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大伙的”。
4)学校大集中,“五化”硬成套,提出七天突击、三天扫尾的口号。
5)大讲卫生,大除四害,并在1958年和59年冬季两次大拆民房,大建新村。
6)1958年深翻土地和59年秋冬大搞万亩丰产方、万头猪场,调劳力、土地、干部、猪羊。
7)在反右倾整风之后,借发展社营经济,大肆平调管区企事业现款、劳力、牲畜、工具。
8)抢过渡,急过渡,盲目扩大管理区。……据统计,1958-60年省专县社四级共平调劳动力760万个,土地1万多亩,肥料99万担,车辆3000多辆,大小农具43000件,粮食132万斤,日常用具42000件,灶具26000件,瓜果菜113万斤,款项599444元,占用民房343691间,拆房屋1377间,……共折款8164637元。其中1959年4月以前占49%,1960年4月以前占30%,以后占21%。省、专、县几级单位和公社、管区,分别占16%、28%、26%、18%和12%。(38) 据说大队平调多为实物,公社平调多为现金,县以上平调多为劳动力和物资。(39) 但是平调退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问题订证”、“作价合款”、“如何兑现”几个环节上,通常都存在“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需经过与“富裕中农”的斗争,才能把问题确定下来。也有些东西并未退赔(如幼儿园和食堂占用的房屋),有的则要到以后“逐步归还”。(40)
在安徽凤阳,“共产风”也一直未停。据1961年初的一项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共折款732万元,人均27元。结果公社化以后,生产连年下降。如凤淮大队三年来粮食产量从157万斤下降到59万斤,总收入从38万元下降到7万元,人均收入从79元下降到4.4元。武店大队的分值也年年降低,1958年社员人均收入37.7元,到1960年降到4.6元,每个劳动日仅值 0.05 元。社员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1960年凤阳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仅有9900万斤,比1957年下降了64%,生猪下降44%。(41)
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高指标、高估产和高征购。
1957年丰收,凤阳实收产量为2亿斤,1958年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9年更提高到12亿斤,超过上年实产量的6倍。连年减产的实际情况,却被说成是增产,1958、59年产量都虚估为4亿斤。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造成了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42)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全县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报告三次,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斗得不狠就是“右倾”。有的公社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层层开会,一直开40多天。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直到1961年中,查粮翻粮仍没有停止,严重的地方普遍查翻。不少大队口粮标准每天只有2两或3两粮食。(43)
从 1959-1960 年,凤阳335698名农村人口中,外流的有 1 万多人,发病的有10万人(主要是浮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和闭经),死亡现象更为惊人,两年死掉6万多人,占人口总数的 17.7% 。有两个公社有 1/4 以上人口死亡,全县死绝 8000 户,死跑而空的村庄 27 个。同时,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60 多起。群众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可以跑,今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从1958年冬,各级党委就成立了“农民外流劝阻站”,配备干部和民兵,竭力杜绝农民外流。(44)
【另见本站补充视频资料:林蕴晖教授主讲:3年“困难时期” ![]() 】
】
据说,1958年受灾后,断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1959年元月调查,某些社3/4的户断了炊,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许多人到外县讨饭。人们开始吃干菜,把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和胡罗卜缨等全收藏起来,烘、晒、晾、炒,做为代食品,粮菜混吃,低标准,瓜菜代。到了1959年秋季,问题更严重了,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1959-1960年冬春,有30%以上的人发病,5万人死亡。1960年秋,消灭了夏季传染病后,浮肿病陆续发展到各乡。丢弃小孩的很多。全县 17.7% 的房屋倒塌了,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45)
【另参见本站补充视频资料:1960 年纪事:北京的食品供应】
1960年夏天在安徽亳县,作家陈登科写道,工作队连夜向省里要钱、要粮,长在地里的绿豆和高粱,还没等到成熟就已吃光。一个原有40户人家的村庄,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60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人们好似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大院。(46)
在山西太谷,春起大人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小孩挖不动,就去寻野草吃,趴在地上,象羊儿一样地啃……(47) 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一个县死亡人口就有 10 万左右,因而被称之为“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48)
随着农民“产权”和人身权益的被剥夺,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极权化,干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实际上,所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强半都是针对干部行为而发的。有的地方问题十分严重,把群众当做奴隶,认为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捆绑吊打、扣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甚至把社员打死、处死。有的私设劳改队,关押外流社员,抓住偷青的小孩、妇女,就毒刑吊打(49) ——以致 1961 年中央试拟“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其中有两项规定: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50)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一些什么反应呢?
如前所述,1958 年“共产风”刮起之后,农民就不怎么干活了。如一律拉平的做法,使许多社员偷懒不去劳动。当时总结归纳有二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髙、干部工作责任性不高;四不清:收的、打的、扬的、扫的不清;十多:粮食糟蹋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加爱护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总之,是“不干”了。(51)
然而这类问题始终没有得以解决,如一直有反映说:“实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饭是自己的,谁还烦鸟神,想办法搞生产?”有的社员说:“多劳不能多得,谁还愿意干!”到饥荒来临之后,生产更处于停止状态,如到地里生产睡觉的多、外流的多等等;1960年的大兵团作战中,有的大队的社员仅6里路就走了3天,消极对抗。(52) ——后来纠正“共产风”时,有的农民指出,过去就是把人“都弄得糊糊涂涂不想劳动”。(53)
这种状况自然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例如土地大量荒芜,如1960年山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草荒现象,6、7 月份全省荒地达到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10 。(54) 在安徽凤阳,据统计,1959年荒田31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21% ,1960年荒田53万亩,占 38% 。最严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连片,甚至6000亩地不立苗,或几里地不种庄稼。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更是普遍现象。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或是瞎指挥的结果。此外,耕畜、农具大量减少,两年来凤阳全县耕畜减少了37%,剩下的瘦弱不堪,农具则减少了35%,约价值70万元,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现象相当普遍。(55) 从全国看,1957年以来大牲畜头数连续下降,到1961年6月底仅有6618万头,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其中下降最严重的便有山东、河南、河北、甘肃、安徽等省。(56)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注释与参考历史文献索引】(1~56) |
|
点击这里展开:本页其余注释——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 【延伸阅读】 |
||
|
||
| (本站 2005-03 编辑转发 / 2018-11-28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