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重读历史>沉重的1957-1965>钱理群教授: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转载)P.3. | | 您好!今天是: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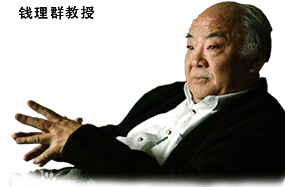 |
|
| 本文作者:钱理群教授 | |
|

| 【“整风·反右”背景研究】 |
1956、1957 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
| 作者:钱理群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
| 作者:钱理群教授 资料来源:爱思想/中国文学网等 本站编辑转载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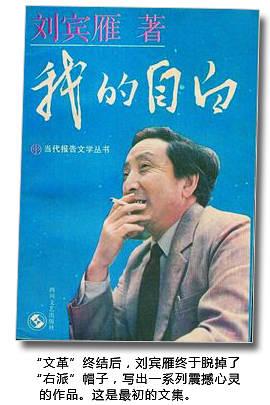 “几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忍耐。
“几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忍耐。
“街上行人的衣着,色彩鲜艳多了。……同八年前我离去相比,物质生活也明显地有所改善。饭馆和酒店中,每天傍晚都有很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豪饮啤酒。
“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城市缺少点什么。或者说,1946年我返回哈尔滨时那个戒严时期的某种气味还继续保留着。它是过于宁静和过于秩序井然了。中央大厅上牌匾的一片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全在党的控制之下。这里有两张日报,编辑们自己都讨厌的每天重复着的同一个声音。
“哈尔滨已从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十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此处疑有错,似应为八年前——引者注)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
当然,刘宾雁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工厂的状况。
据他的观察,“全国都把注意力放到工业上,主要又是重工业。1956年是一个高峰,从中央到基层厂矿与建设工地,都照例热衷于速度,它的标志就是产值。工人的热情仍然很高,也仍然很听话。为了完成计划,常常必须连续加班加点;有的青年工人甚至不经领导同意,偷偷加班干活。同时业余时间还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定为制度的文化学习也不能缺课。疲劳,过度疲劳是普遍存在的。这就使工伤事故增多了。”
但这样的劳动积极性背后,也还隐含着一些矛盾,以至危机:“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和阶级斗争的淡化,对于前些年颇见成效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人们已经开始淡漠了。同时,工人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与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很迟缓”,“哈尔滨的物价指数那几年每年上升将近15%,而工人的工资却已有几年没有提高。拿二、三级工的工资而做四、五级工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几年收入不变,甚至临时工干了七年仍不能转正,工人们就只有不断压低自己的饮食水平了。有些人只能吃粮而不能吃菜。……哈尔滨的有些青年女工必须积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块花布”,问题是企业领导还要压低工人的工资(这里的特殊情况是,“企业在提高职工工资上权限受到限制,要压低工资却是可以自主的”),因为“企业的工作成效,以上缴国家利润多少为定,压低职工工资,便可降低产品成本,企业领导人就可以上缴更多的利润,从而博得上司的好评”。
得不到基本的物质保证的矛盾在青年工人中尤为严重,反映也更为强烈:“新住宅七级以上的工人才能分到,与他们无缘;男青年找配偶很难,很多人必须跑到千里以外的家乡去找,有了对象又愁没有住房;于是发生婚前性关系以至女方怀孕的就多了起来,而老工人旧道德意识很强,这些青年就成了嘲讽和谴责的对象。所有这些现象都很容易地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青年人想转入条件较好的工厂,甚至想报考中专或大学这一类合理要求,……都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作为教育和批判的对象。至于对领导人工作中的错误的正当不满和批评,则往往要受到更严厉的压制”。
这样一种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到工人与干部、党和国家的关系。团市委的干部告诉刘宾雁:“我们成天对青年工人讲,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发挥主人翁精神。但在一些工厂里,工人根本不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已经出现多起工人盗窃工厂物质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困难了”。一位工人对刘宾雁这样说:“过去出点事,总以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现在一听说出了事,马上就责怪说:这些领导干部是怎么搞的!”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刘宾雁来到哈尔滨电机厂,并贴出告示,公开自己的住处,“欢迎青年职工(直接)来谈”。“几天中间,到住处找我反映意见的总共不过二十几人,而这家工厂有职工近万人。他们的不满,用三十年后的眼光看,也都是些小事:工作安排不当,或没有固定工作;评工资级别不公正;住房分配上厚此薄彼……等等”。但一位姓梁的工人代表及很多人来反映的情况仍使刘宾雁受到了震动。他话说得很慢,也很激动:“我们也是人,可是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从技工学校毕业都两年了——这种人工厂里有二百多,可是到今天也没有正式工作,老是打杂。甚至去做清洁工。我们去找干部:工程明明不需要这么多人,让我们到辽宁去行不行?那边工厂缺很多人。不行,宁愿让我们闲得慌。理由是:把你们放走了,万一明年工厂的任务扩大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可若是不扩大呢?我们这些活人便成了货物了,长期储备在仓库里。没有固定工作,提级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什么都耽误了,比如结婚……”。“将人当作货物”——这大概是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甚至工业化的某些本质的。刘宾雁最后将他的调查结果概括为两点:“当时(工人)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严密注意的迹象”。——刘宾雁对1956年中国工厂状况的这一观察,对我们理解一年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自然是重要的。[24]
1957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由中共中央直接发通知及其用词,都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说,“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1956年10 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的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25]
罢工、罢课的具体情况至今仍未公开,不过中共中央的《通知》中还是多少透露了一点信息,其中有两段话就大可琢磨:一是“由于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校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另一是“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26]
联系刘宾雁当年所作的前述调查,就不难理解:罢工、罢课所要维护的是个人的被忽视了的物质利益,所要反抗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与特权。
毛泽东在1957年1月的讲话中还这样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的罢课游行:“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有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按毛泽东的描述,这样的罢课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且是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反响。因此,毛泽东又有这样的分析:“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感恩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27]
这几乎已经预示了后来的反右派运动。
但在1956年的下半年与1957年初,毛泽东还同时把罢工与罢课的发生归结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甚至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即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28]
——从这里可以看出,1957年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开始的整风运动,还是后来的反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人、农民与学生“闹事”的反应,而这样的“闹事”又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始终存在着一个“中国会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的阴影。
而且这样的“闹事”到1957年仍在继续。
2 月份毛泽东在他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纲)》里,写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29](1956年1 月,在对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毛泽东透露,当时中国城市里还有一百万的失业人员)。[30]而研究者则指出:“在1957年初,城市失业问题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前一年秋季的歉收和合作化带来的混乱,使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政府机关的精简运动,比平常多的复员军人数目,以及减少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人数的措施,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31]
这样的失业与失学问题自然是极容易引发“闹事”的。
这一年5月13日(这正是鸣放达到高潮,毛泽东也在准备反击的紧张时刻)《人民日报》以《谈职工闹事》为题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说:“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正如以后的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社论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例。某些企业是哪些?最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32]
《人民日报》社论着意含糊其词的事实,30年后,在刘宾雁的回忆录中得到了部分的揭示。正是1957年4月,《中国青年报》编委会上社长张黎群传达刘少奇的一个指示: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于是,刘宾雁被紧急派往上海,与报社驻上海记者陈伯鸿一起进行采访。由于全国形势很快就发生了激变,采访也自然不了了之,但留下的记忆却历经风雨而难以忘却——
“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我和陈伯鸿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和许多工人、各种政治态度的党员与干部、群众、领袖分别谈话。我们认为这个工厂党组织的危机对于唤醒全党警醒,痛切正视执政党的危险是极有意义的。
“从1955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这是因为党大体只发展两种人入党:听话而不说话的人,并无入党要求因而也不起作用的、为分享执政党的利益而巴结干部钻进党内的人。前一种人帮不了党的忙,而且纷纷退了党;后一种人则只能害党。党员中也有好的,愿意为工人的合理要求说话,却遭到领导的申斥,被认为‘党性不强’。同时工人又认为党员应对各种不合理的事情负责,骂他们是‘白鼻头’,把他们当作工贼。在工资、借款、评级、困难补助、竞赛评奖等方面,都厚此薄彼。工人的困难无人过问。甚至有的工人被生活所迫要自杀了,工会仍然不管。一个洗澡用水的问题就不知喊了多久。写了许多信给党的区委和报社,一概石沉大海。
(未完,点击:接下页)
【本页注释】
| 24. | 以上引文见刘宾雁《刘宾雁自传》,75-80页,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 |
|
| 25. | 《毛泽东传(1949-1976)》,611-6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 26. |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注释(1),37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27. |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332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
| 28. |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12-6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
| 29. |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3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30. | 《对廖鲁言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2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31. | 参看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任命共和国史》,2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
| 32. |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
【相关链接】
1、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4、1955 年纪事之十四:冒进——“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8、【搜狐大视野】“天堂”实验: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记录与述评)![]()
10、林蕴晖教授主讲:1958 年的“大跃进”【历史讲座视频】![]()
11、林蕴晖著《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
12、张一弓1980 年获奖小说:《罪犯李铜钟的故事》(纪实性小说)
13、【本站编辑】“人民日报”上的“整风-反右”历史记录(鉴赏“右派”言论)
【附】 【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建国60 年纪事】目 录(选)
|
|
||
|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6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