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陋室文化/历史钩沉>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说/转载)- P.5. | | 您好!今天是: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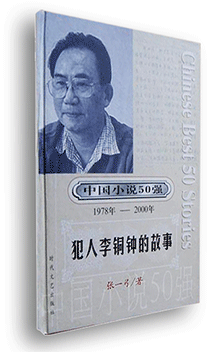 |
|
点击:到“历史钩沉”栏目…
时评杂谈
点击:到“重读历史·沉重的
1957~1965”专栏
…| · 1980 年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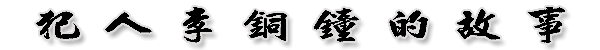
作者:张一弓 |
| 作者:张一弓 来源:《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中篇小说卷一 / 豆瓣小组(网络) 本站转载 |
| (点击这里:承前页) |
九、饲养室里
在三队饲养室,李套老汉已经把两头辕骤和四头帮梢牲口交给了鞭把,正满心欢喜地向他平些拴在槽上的臣民们宜布:“统销粮来了,你们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
李铜钟、小宽跟一队鞭把二愣,掀开棉门帘走进来。小宽向铜钟使个眼色,说:“套叔,你看,一队社员来向你取经。”
李套老汉从槽前勾回头,说!“咦,还没吃上一顿饱饭,可又取经哩!”他对风行一时的“取经”很有点信不过。
二愣说:“灾荒年景,俺一队见你喂那牲口老壮实,把大车又套上了,不知你用的啥仙法儿。可俺队牲口不争气,凑合着只能派出去一辆车。大家叫我问问套叔,你这牲口是咋喂的?”
“咋喂的?”李套老汉心里像三伏天用小扇子扇着。“牲口不会说话,全靠人替它操心。”他看看儿子和小宽,“实话说,我给你们当千部的守了点密。秋后,我看着粮食紧缺,就天天省下几把料。”他掀开草垛,露出几个料布袋,说:“这不,到如今,这群吃材虽说料不足,可没断过顿。啥经?就这。”小宽说:“咦,你对俺铜钟哥也守密?”
李套瞟儿子一眼,说:“他牲口都舍得吃,能不吃我这牲口料?”他想起了“花狸虎”,可怜它没能熬到今天,心里又难过起来。“可也难怪你们。我是喂牲口的,是把牲口看得高些儿。社会主义是辆车,全靠大骡子大马拉着跑哩!” 李铜钟感激地望着老爹,他想起,食堂里还能打来一瓢稀饭的时候,爹时常等送饭的媳妇走后,把稀饭倒在牲口槽里。
小宽看时机成熟了,笑着说:“套叔,眼看要去拉粮食,可一队牲口有困难……”
李套心里一沉。“你是说使咱这牲口?”
“套叔,俺队社员说,不使你喂这牲口,粮食别想拉回来。”二楞嘴上像抹了蜜。
李套老汉坐在草垛上,想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才开腔说:“我能眼看着粮食拉不回来?可我这牲口也不是老硬邦,这四爪马跟那个骡子,勉强能驾辕。既然你们当干部的事先拍了板儿,我一个喂牲口的还能挡车?”
没等李套老汉说完,二楞就去槽上解缰绳。“等等。”李赛老汉用烟袋锅点着二楞的鼻子,说,“你们那帮梢牲口可得硬邦点,你们当鞭把的不能鞭打快牲口。”
“套叔,你看看。”二愣掀开棉袄襟子,指着肋条说:“就是叫我甩扎鞭,你侄儿我也没那力气。”
李套郑重地看看他那二九一十八根肋条,那确实是二九一十八个可靠的保证。他终于解下了缰绳。
小宽、二愣把牲口牵走后,李套老汉又叫住儿子,说:“听说粮食不算少,可你记住给社员讲讲,囤底儿省,不如囤尖儿省……能吃半顿,不叫断顿;不能有了粮,没了忍。”老汉又心疼地打量着儿子,“这些天,难为你了。等粮食拉回来……”他指着儿子的假腿,“叫它好好歇歜,是根拐棍儿也不能整天拄着。”
“中,爹,等粮食拉回来……”铜钟想起了什么,神色怆然地说:“我跟它都歇。”
“是这话,为群众跑腿儿,天还长着呢!”爹说着,背着手,向槽前走去。
十、寨门外的呼喊
西寨门外大路上,摆着大车小辆。由基干民兵组成的运粮队,在一人吃了两碗萝卜熬白菜以后,已经排好队站在寨门涧里。
李铜钟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要遵守纪律,到了粮站,是给咱的咱拿走,不是给咱的,一粒粮食子儿也不能拿!第二,不要坐车,叫牲口留着气力拉粮食!第三,黑更半夜的,不要惊动四邻八家。
在积雪映照着的靠山公路上,人马出发了。“你坐上,你那腿不得劲。”有人在铜钟耳边说话。这是张双喜。
“你不该来。”李铜钟有点生气。
“我陪你,到天边儿,我也陪你。”“咱队委……都陪你。”这是崔文的声音。星光下,李铜钟看见十几个人影,无声地簇拥着、跟随着他。他不满地叹了口气,颠拐然而坚定地向粮站走去。
“不能去呀,不能去呀!”寨门里,传来老杠叔嘶哑的哭喊声。他跌跌撞撞地奔出寨门,跌倒在路旁的积雪里,但他扒着,爬着、喊叫着:“孩儿们,回来呀……咱饿死也不能动公仓。
—阵山风卷走了老杠叔的呼唤。
李铜钟头也不回地走着。他觉得有一条小虫子从他眼角里蹦出来,那是一滴只有在人们看不见的时候才让它流出来的共产党员的眼泪。
大路上,没有人声,只有“嘚嘚”的马蹄声。
十一、“毛主席,请您老人家原谅……”
沉默多天后,李家寨的三座磨屋里又响起了轰隆轰隆的磨面声。磨屋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按照连夜分配到户的口粮指标,每户先领一天的面,让全村人赶紧吃上一顿饱饭,然后随磨随领。
石磨在轰鸣,老杠叔却在叹息。小宽从西寨门外把他背回来以后,他就躺在床上,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咋办好哩?违法粮吃不得;不吃违法粮,眼看要饿死人啦!你活了六十多,土拥住脖子了,闭住嘴不吃这违法粮,当个干干净净不犯法的鬼去。可全村四五百口,都叫跟着你,啃那墓坑里的土?
但是,在大多数七天没吃一粒粮食子儿的庄稼人看来,对于他们必不可少的肠胃运动和衰弱到极限的身体来说,违法粮跟合法粮没有年何区别,或者可以说是同样的“老好”。营养学家可以作证,玉米,无论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它所包含的蛋白、淀粉和含热量完全相同。
正是这缘故,磨屋前才排着长长的队,一张张浮肿的面容上都已餺出宽慰的微笑,一双双昏黄的眼膪里都在闪耀着生命的光芒了。就连老杠叔的百依百顺的老伴,也好像完全不明了老杠的心思,已经以烈属的身份站在领面行列的第一名了。
违法粮同时又是救命粮,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分裂,使得老柱叔越想越糊涂了。而这时,崔文在门外喊叫:“老杠叔,磨屋里堆不下恁些粮食,还得用用食堂庠房,小队保管立等你开锁!”
老杠叔必须马上决定对这批违法粮的态度了。他“吭吭”地咳嗽着,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老杠叔,我在一队等你。”崔文忙得脚不沾地,没进屋就走了。
咋办好啊?法律与营养的矛盾逼得老杠叔无路可走了。他从床上爬下来,站起,又坐下;走两步,又返回来,最后,才想起什么,摸摸索索点着了灯,举在手里,照亮了墙上的毛主席像。两行热泪“噗嗒嗒”落下,滴在土改时分的那张八仙桌上。“毛主席,您老人家就原谅俺一回……”他哽咽着,对着毛主席像说,“咱李家寨的干部都是正经庄稼人,没偷过,没抢过……锏钟是俺从小看大的,去朝鲜国打过仗,是您教育多年的孩子。……俺吃这粮食,实在是没有法子……”老杠叔不可遏止地痛哭失声了,他丢下油灯,“噗通”跪下,说:“毛主席,当个人老不容易呀!您就原谅……原谅吧!”老杠叔“呜呜”地哭着,好久,才抬起苍白的头,透过蒙胧的泪水,望见毛主席慈祥地向他微笑。他哆哆嗦嗦地擦去眼泪,吹灭了灯。
在夜色笼罩的村巷里,老杠叔拄着棍,颤巍巍地走若。“原谅……原谅……”伴随着钥匙的叮当声。
十二、三 口 大 锅
整个村寨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里,李铜钟和他的假腿,却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床下,酣甜地睡熟了。
只是在平安地拉回粮食、磨屋里响起轰鸣声、社员们开始把黄澄澄的玉米面掂回家里的时候,李铜钟才忽然感到那样衰弱和疲累,多天来一直在右肋下折磨着他的疼痛,断腿骨朵上磨出的新的伤口,都忽然变得那样难于忍受了。他感到必须睡一个好觉,才能有足够的精力,让那条假腿把他带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翠英跟社员们一样,还不知道这批粮食的秘密。她喜气洋洋地和婶子、大娘们厮跟着,领口粮去了。为了让男人睡个好觉,她把囤儿送到饲养室,交给了公爹。恬静的小屋里,只有铜钟在说着梦话:“是我……我是李铜钟……”
铜钟睡来时,已经过晌午了。屋子里弥漫着白茫茫的水蒸气,荡漾着玉米面馍的甜香。翠英却坐在灶边,悄悄地擦着眼角。“翠英,你?……”
翠英把几个玉米面馍、一大碗黄糊涂端到床头桌上,说:“全村人都吃了一顿饱饭,就剩你了。”她说着,把脸偏到一旁。
“翠英,你哭了?”
“吃你的吧。”翠英避开了铜钟的眼睛,“煤火不老好,我加了把柴禾,烟熏住眼了。”
是哩,庄户人家有了粮食,喜欢还来不及呢,哪有哭的道理?大口大口地嚼起来。“好吃,好吃!”他连声称“你做的是糠吃着也香,这可是成色十足的玉米面。”
翠英悲伤地瞟他一眼,又低下头,把两块玉米面馍用手巾兜着,又用勺于刮着锅底,舀了半瓦罐黄糊涂,掂着出了门。
“翠英,才给咱爹送饭?”
“爹吃了,囤儿也吃了。”
“那你是往哪儿掂?”
“别问了,你吃一顿安生饭吧。”
“谁家出啥事啦?”铜钟在找他的假腿。翠英停下脚步,眼圈红了。“我去寨外拾柴禾,碰见一个逃荒的……”
“逃荒的?”铜钟心里一沉,他明白,他这个逃荒逃到李家寨的屋里人,老爹是饿死在寨壕里的,她懂得逃荒的艰难。铜钟忙推开碗说:“那你快送去。”
翠英刚出屋门,铜钟就套上了假腿。当铜钟来到西寨门时,只见一个花白胡子老汉,抱着一根棍,倚着铺盖卷儿,歪倒在寨门洞里。翠英正一口一口地给老汉喂饭。老汉身边围着一圈社员,正把一块块刚蒸好的黄面馍塞到老汉的破竹篮里。老汉已经缓过劲来,直起身子说:“谢谢,谢谢!”铜钟问:“大爷,你是哪村的?”“柳树柺。”
李铜钟想起了刘石头和他的“一口酥”,拿定主意说:“大爷,不要走了,我给你挖点粮食,送你囬去。”
“多谢了。”老汉用棍指指寨门外,说,“俺后头还有上百口子,不能都麻烦你。”
铜钟走到寨门外。他看见一个无声的人群正在北山脚下缓缓移动着。有人背着铺盖,有人挎着篮子,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的山路,移动着,吃力地移动着。
走在前头的那个人,肩上挎着铺盖卷儿,手里掂着一个小广播筒,不时地勾回头,把广播筒扣在嘴上喊叫:“不敢掉队,不敢掉队!”
“石头!”铜钟喊叫那个领头的。刘石头装着没听见,低着头,不看他。
铜钟迎上去,把石头拉到路边,说:“你这个支书,领着社员上哪儿去?”
刘石头没好气地说:“你就别叫我支书,你就叫我要饭头。支部决定了,出外逃荒,也得书记挂帅。”他牲铜钟一眼,忽然把帽子抹下来,像碗一样捧在手里,行着鞠躬礼,说:“行行好、行行好,同志,您就留一口,留一口,留个碗底儿叫俺舔舔,叫俺这种粮食的人舔舔……舔舔……”刘石头学说着,不由地眼圈红了。
李铜钟一把抓过帽子,给他戴在头上,说:“咱说正经话,你们在这儿避避风,李家寨送你们一人两碗黄糊涂。”
“咦咦,你那粮食不敢吃。”
“为啥?”
“吃了会吓死俺1”石头又朝铜钟瞥了一眼,说,“你们会计媳妇是俺村闺女,今儿淸早,她掂回去一手巾兜玉米面,她说……”石头用胳膊肘碰碰铜钟,“老弟,你打过仗,胆大!”
铜钟说:“不管咋说,这两碗黄糊涂,你们非喝不可!”石头说:“椿树坪、竹竿园也有一、二百口逃荒的,一会就过来,你管得起?你不知,眼下趁公社干部都在县里开会,光咱十里铺公社,就有几千口人去卧龙坡扒车。”
李铜钟心里乱了。他在想,李家寨的人不挨饿了,可还有多少柳树拐、椿树坪啊!……
转眼到了寨门口。李铜钟抓过来刘石头的广播筒,对柳树拐的逃荒社员说:“婶子、大娘、大叔、大伯们,你们路过俺李家寨,李家寨也没啥送你们,就在这寨门洞里避避风,给大家熬几锅黄糊涂,喝了再走。”他把广播筒还给刘石头,就一颠一拐地朝寨子里奔去了。
村巷里,才吃了一顿饱饭的庄稼人商议着:“一人省下二两,送送咱那荒的乡邻吧!”
就这样,李家寨西门外支起了三口大锅。锅里煮着稠玉米糁,勺子搅不动,祺子挑得起,一人两大碗,送走了柳树拐、椿树坪竹竽园的逃荒社员。
天黑了。走风口吹来的寒风,猛烈地摇落了树上的积雪,天黑得像倒扣着的染缸一样。不知是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雪了,鹅毛雪片在风中狂舞,淹没了逃荒的人群。
据喇叭碗里的气象预报:今夜大雪,北风七级,最低温度零下十五度。想着那个小车站上的逃荒社员,李铜钟心里结冰了。
(未完,接下页:“首犯是这样落网的”…)
【延伸阅读】
2、【凤凰/腾飞中国60年】1958年纪事:农民与科学家竞赛放“卫星”
4、【建国60年纪事】1956年纪事之一:对峙——冒进与反冒进
5、《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1959.8.10.)
| (本站 2005-08-19 转发 / 2018-02-15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