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本站评论>【转载】读史: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山东饿死人真相(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读史: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山东饿死人真相 |
· 新浪推荐博主/秋月朗 · |
| 来源:新浪博客推荐博文(2015-11-23) 作者:秋月朗(新浪推荐博主) 本站转载:(2019-02-20)(浏览: 人次)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原文题记】这是当年新华社下放干部张广友讲述的经历和见闻。 |
※ 灾 区 系 列 调 查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
离开了张店,很快就进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地广人稀,空旷的原野上目无遮挡,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地。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看到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在运地瓜蔓。时过冬至,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一轮红日就已经落入地平线,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凄凉,很快给人一种到了灾区的感觉。晚7时,摆渡过黄河,到了北镇。从张店到北镇,说是160华里,车行了3个多小时。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新兴小城镇,原属滨县。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什么都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就把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了,地区所在地设在张店。与此同时,也把惠民县同滨县合在一起,北镇就成了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区所在地是在北镇,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后不久,又恢复原来的地、县建制,北镇仍为惠民地区所在地,而惠城仍为惠民县委所在地。
北镇招待所是一排排红色砖瓦平房,看来是新盖不久,似乎没有住过人。屋子里空旷潮湿,没有生火,冷得很,冻得我一夜没怎么睡着,当了一夜“团长”,早上早早就起来了。这里每天两顿饭。早饭9点,每人两个地瓜面窝头,白开水就咸菜;晚饭下午3点,也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在北镇招待所住了两天,顿顿如此。地瓜面窝头北京没有,过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发褐,很瓷实,硬得像块砖头,表面有些光亮。刚吃时,咬到嘴里有一股汤药味,难以下咽。头一顿吃不下去,后来就不够吃。虽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没得吃只好如此,逐渐也就适应了。可老百姓连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镇待了两天,听听惠民县领导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研究我们下去的具体地点和任务,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到惠民的,先安排到两个公社的两个大队:一个是桑落墅;一个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队,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队。
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了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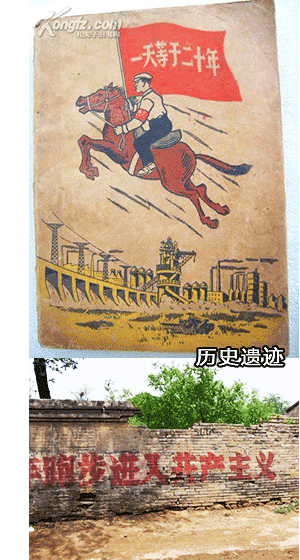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
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
“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4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
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屎尿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粮食紧张是带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虽然供应也很紧张,但比起其他地方还是好得多。虽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凭本、凭票,但样样都还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两糖、半斤点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证。我来山东灾区之前,家里听说了这里吃不饱饭,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离开那天,家里人把全家节省下来的几两糖果和几块点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里,嘱咐我说实在饿急了就吃一块。
那时规定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灾区人民实行“三同”,但这是家里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带来了。下来已经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没有机会吃,所以一直没有动。这次我把它拿出来偷偷给了房东,叫他们给这个孩子吃。他们一方面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晚了,吃什么都不行了,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说:我留着没用,还是快给孩子吃了吧,试试看或许能解决点问题。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收下了。此后不久,我就离开这个村子了,后来究竟起没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毕竟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这件事按当时说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当时规定下放干部绝对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带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向任何人讲,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对那时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的吃,给我吃什么?
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 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
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
 |
| 1958年,举国上下全民“大炼钢铁” |
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爆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
 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社员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
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社员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
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于是后边一群人也都跟着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
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1961年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重点是: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的惠民县委,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县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我们下放干部又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做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可以,遂决定我们到灾情严重的胡家集公社,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了胡家集公社。我被分配到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胡家集公社离县城70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在我们到达胡家集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3里多路的皂户杨生产队。我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目无阻挡,一片片平坦的耕地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属于“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的一部分。本来是想引进黄河水灌溉,促进农业生产,但没想到引进的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庆吉,但走了一家又一家,不见一个人影。最后,好不容易碰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经她指点,才算找到了杨庆吉。
杨庆吉如实向我反映了该生产队的灾情。按照县四级干部会议的精神,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我到皂户杨生产队后中心的任务是抢救危重病人。我逐户走访了这里的每一家,并对这里的50多名危重病人采取了措施,把他们送到大队疗养院治疗。对那些自己还能够生活的重病人,把补助粮和代食品送到他们家,口粮每天不足6两的一律补足6两,达到6两但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再补助一些棉子饼、地瓜蔓等代食品。春节前每人还补助了2斤面粉,让家家春节都吃上了水饺。群众非常高兴。
在大于公社包队蹲点的生活
1961年3月下旬,我们离开胡家集公社,来到大于公社。大于公社是惠民城区一个比较小的公社,有5个大队(即5个自然村):朱老虎、大孙家、李中条、吕家台、大于,共5000多人口。公社的名字虽然叫大于公社,但其所在地却是朱老虎村,因为它处于公社的中心。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有4个人被分配到这个公社分点包队。领头的是国际部干部于中干,他已被任命为惠民城区委副书记,他有时和我住在朱老虎村、大于村;对外部的黄龙和国内部的周淑琴住在大孙家村。
大于公社的灾情出乎我们的意料,十分严重。虽然靠近县城,但在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和其他公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如果说相对好一点,就是靠近县城的两个村,可以到机关食堂和饭馆捞泔水、拾菜帮子充饥,其余三个村灾情十分严重,其中以朱老虎、大孙家最严重。
我们在大于公社包队蹲点首先遇到的是住的问题。黄龙和周淑琴是大孙家村的包队干部。周淑琴是女同志,她被安排到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黄龙的住宿遇到了很大困难,住在群众家里一间没人住的空屋子里。当时天气还很冷,把全部铺盖都用上,也时常被冻醒。黄龙是归国华侨,当时48岁,在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中年龄最大,而且对北方农村的情况也不熟悉。我们对他的住宿问题都很担心,但几天后我去看他时,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面,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不相信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我探头往棺材里看了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面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的确不会太冷,但把活人逼到死人住的地方,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在大于村包队,住的条件稍微好些。我到大于村时,正赶上村里的粮库第二次被盗,仓库保管员说什么也不干了。大队长刘振西就把我安排在仓库保管员住的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这里的种子可是全队的宝贝啊。你是从北京来的,全队社员都信任你。这里有个土坯炉子,天冷可以找点柴禾生生火,烧点水。他说完后,我说,住在这里可以,但我没有看仓库的任务,不能保证粮仓不被偷盗。刘振西赶忙说:“那是,那是!”就这样,我在大于村住了下来。
我们在大于公社包队蹲点,不仅住的方面遇到了困难,更困难的是吃的问题。我们下放干部是带着户口下放的,口粮按当地干部的标准定量供给。惠民是个重灾区,我们每人每月供应17斤地瓜干。我们虽然带了一些全国通用粮票,但按照不搞特殊化的规定,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比当地干部还苦,他们都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多,有回旋余地。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我们就开始浮肿了,腿上、脸上一摁一个坑,好长时间起不来。
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彼此同甘共苦,互相关怀,非常团结。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惠民县的领队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任丰平。他是行政12级干部,当时按规定,13级以上的干部,每月补助一斤白糖、一斤黄豆、二斤鸡蛋,粮食定量中50%是细粮。他的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但很少吃细粮和鸡蛋,等我们到县里开会时,他给每人发一个鸡蛋,并用他的馒头票给每人兑换一个地瓜窝头票。有一次,任丰平的警卫员偷偷对我说:“任书记也浮肿了。他仍旧把细粮和鸡蛋节省下来,说你们下边比他苦,留着你们来时给你们吃。我劝他先吃些,你们来时我去找伙食管理员给你们调剂点儿。他说啥也不同意,还说不能带头搞特殊化。”我听后,立即到他的办公室问他:“丰平同志,听说你也浮肿了?”他说:“没事儿,没事儿!”那天,我心情十分难过,连晚饭也没有在他那儿吃,流着泪偷偷地回去了。
扭转形势的关键措施
阳春三月,冰雪融化,春回大地,万物苏醒,也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生机。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下放干部和当地干部一起,为搞好1961年的春耕生产,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要求,依照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有关规定,在惠民县重点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农业合作化初期,惠民县的农民都有自留地。自留地名义上是种菜的,实际上在粮食紧张的时候,大都种了粮食。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自留地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1961年春耕前,全县全部恢复了自留地,没有或不足的,重新予以划给或补足,并宣布谁种谁收,不计征购。根据县委的意见,下放干部根据本人的意愿,也可以按照当地农民的标准,划给一份自留地,由本人耕种,作为生活补贴。同时,也恢复了集市贸易,一直偷偷摸摸的私下贸易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了。
二是调整生产队规模,实行生产队核算,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紧急指示信》中反复强调的。按照这个精神,全县首先调整了生产队规模,普遍划小生产队,户数比原来减少一半,一般一个生产队是20至30户,而且每户的人口比过去减少,一般是每户平均3人左右。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合得来,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合力。在调整生产队规模的基础上,全县贯彻落实了“三包一奖四固定”,普遍实行以产量定工分、按工分分产品的办法,比较好地落实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三是实行“以粮代赈”。所谓“以粮代赈”,就是在春耕生产中,对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社员,每天予以一定数量的粮食补贴,一般是每出一天工给半斤补助粮。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是反对特殊化,强调社队干部(包括下放干部),特别是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时要利用业余时间种好自留地。
我们在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中,感到效果最明显的是恢复自留地。按照规定,社员(包括下放干部)每人三分自留地,自留地种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正因为这样,社员群众都精心种植自留地,既种菜又种粮,采取间作、套作等各种方法,地上地下结合,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使它发挥最大效益。我在下放期间,种了两年自留地,对此深有体会。正如一些农民所说的:“自留地这个尾巴不能割,割了会死人的。”
在种好自留地的同时,由于措施得力,在没有牲畜、农具奇缺的情况下,社员群众完全凭着自己的双手,把绝大部分荒芜的集体土地按时种上,从而使春耕生产进展顺利,夏季取得了好收成,形势开始扭转,“五个月工作的转变”的要求初步实现。紧接着又乘胜前进,取得了秋季的好收成。丰收了,社员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浮肿、干瘦病大大减少,非正常死亡停止,农村出现了生机,农民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由于政策稳定,1962年夏季又取得了好收成。整个惠民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于公社形势更好。我非常高兴,当年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的:“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于公社今年夏天有了余粮了。大于大队是一个先进大队,全队夏粮总产达到4万斤,平均亩产达到180多斤,每人可分到口粮150斤左右,再加上自留地、开荒地,每人可收200斤左右。”
※ 关于“包产到户”的调查
1961年,农村发生的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原因在哪里?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这是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反对“五风”的可喜成果。但是,我们在下面深深感到:群众对《紧急指示信》中的各条内容的反应差异很大。其中,有些是群众迫切要求、非常欢迎的,如:“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允许社会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有些则是群众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的,如:“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办好公共食堂”。还有一些规定对重灾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从各方面节约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等等。
1961年初,毛泽东派出3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调查《紧急指示信》的贯彻落实情况,发现了不少问题。接着,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着重解决各生产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明确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同时在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这对进一步解决农村问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对安徽农村出现的“责任田”的支持。7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可以试一试”。这样,“责任田”在安徽大面积推广。到1961年秋末,安徽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了85.4%。(【本站评注】实际上,毛后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为此而高举起“阶级斗争”大旗……成为日后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点击这里:浏览党史百科)
“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
在安徽出现“责任田”的同时,山东的一些重灾地区的群众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我们在1961年春组织群众进行春耕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种苗头。有些大队在划小生产队规模,实行包工包产、不征不购的同时,实际上搞了包产到户。这些重灾队原来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就比较多(人均三亩多),再加上近两三年人口有所减少,许多耕地没人耕种,已荒了好几年了。与其荒,不如包下去,谁种谁收。对此,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因为包产到户被作为资本主义明令禁止,所以大家心照不宣,都叫“三包一奖”。
1962年春,在安徽“责任田”的影响下,惠民县少数社队,从偷偷搞逐渐发展到半公开、公开搞包产到户。大部分社队在观察领导态度,想搞不敢搞,而县社两级领导干部,态度暧昧,采取了不接触、回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1962年7月初,我回京休假,新华社国内农村部负责人于长钦和内参部主任夏公然询问我所在县和公社包产到户的情况。我说,因为没有见诸于中央文件和领导指示,我们公社没有公开搞,惠民县有的社队搞了。不久前,我被派到附近的小郭村公社李家店大队做过调查,写了一篇《李家店包产到户调查》。县委第二书记任丰平把它作为县委《参阅文件》向全县转发了。夏公然听后要我马上整理出来给他,准备在《国内内参》上发表。
我很快把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夏公然和于长钦,他们看了很高兴,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的栏题下,头条位置编发。稿件编好上了版,但是编辑部有关领导觉得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拿不准,决定送中央审查。但风云突变,毛泽东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把包产到户批之为“单干风”(点击这里)。从此,包产到户成为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再度遭到批判。我这篇调查报告从“很好”也变成了“很糟”。我虽然当时被夏公然保护过关,但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历史“污点”,几乎每次运动都为此检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1年我这篇调查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编入《包产到户资料选》,成了农村改革的重要参考资料。
1962年9月,我奉调返回北京新华社总部,从而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山东惠民,结束了近两年的下放生活。 █
| 【相关链接】 |
||
| (本站 2019年02月20日发布 / 2019-03-02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