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文革研究>【转载】范达人: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 徐唯辛与他的肖像作品:王容芬 |
| 【转载自“腾讯网”网 2014-08-10 文章】 |
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
| 撰稿:范达人(原发《炎黄春秋》) 来源:“腾讯网”网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梁效”是按毛泽东要求建立的一个“批林批孔”写作班子的笔名,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些教师组成,此笔名当为“两校”的谐音。毛泽东的联络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刘冰是“梁效”写作组的直接领导。但刘冰是受谢、迟压制的,范达人在本文末所附视频链接中介绍了这一纷争的具体情况以及毛、邓、江之间的矛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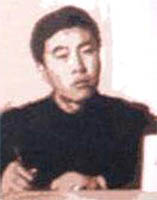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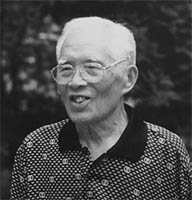 |
| 约1950年代末,谢静宜与毛泽东 | 迟 群 | 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 刘冰 |
在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被视为党中央声音的传达者和“毛泽东思想、意图的诠释者”——当时的段子“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既反映了党媒的“舆论一律”,更反映了“梁效”文章的权威性。
六、想离开“梁效”
大约在1976年4、5月间,宋柏年召开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大会,对李家宽、王世敏两人的工作作风进行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此会,并支持大家对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大批判组,回原单位工作。
那天,我正好回家,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事后,有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李、王二人调离后,宋柏年担任“梁效”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郁龙余和中文系的孙静进入领导班子。北大党委书记、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和北大党委常委魏银秋得知此事后,认为处理欠妥,强调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风或其他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但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应调离“梁效”。迟、谢考虑了王连龙和魏银秋的意见,两三天后,又将李家宽和王世敏调回大批判组并官复原职。
1976年春,我的妻子从波兰回国休假。为便于工作起见,她希望我同往华沙。我也想乘机离开“梁效”。我向“梁效”领导打了报告,要求随妻赴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请调报告先交给李家宽,再转送迟群、谢静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党支部、校党委和迟、谢一路绿灯,旋即获准。当时,我以为领导通情达理,照顾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位头头告诉我,迟群生怕我把“梁效”的情况泄露给外交部,曾几次说:“让范达人走吧!”由此看来,我的请调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不过,我并没有调成,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赶上了华国锋下令查封“梁效”。
七、“梁效”终结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但我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到10月10日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
当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我,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我心里一震,说怎么就这样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我将迟、谢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
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灯光很亮,很多吉普车、摩托车,军队把“梁效”住地包围起来了。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头。一个为首的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我们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从这时开始,“梁效”成员受到严厉审查,写材料,交代问题,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我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八、从严发落
1976年10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写揭发、交代材料之际,历史系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边喊口号,一边敲着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下游斗李家宽、王世敏和魏银秋。李家宽的脖项上挂着“梁效”头子的木牌,王世敏则挂有“江青的女状元”字样的牌子。魏银秋因为来自八三四一部队,因此,胸前牌子写的是“通天人员”。
由于文革初期我有挨批斗的经历,因此,当时的心情并不紧张。这一天似乎还讲政策,并未把我揪出来,尽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较突出,罪名不可谓不大。
可是,好景不长,之后,我被批斗过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学生和年轻教员揪斗过,也被历史系揪回系斗过几次,既有大会,也有小会。
后来,清查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争逐步升级。从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开会学习和写交代材料外,其余时间无人看管。此时则不然,平时我不得随意离开红二楼。我的妻子受到牵连,突然从驻外使馆被调回。虽然对我不断施压,但过了一段日子,清查组大失所望,认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问题,而态度甚至比以前更坏。1977年3月,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北大革委会副主任黄辛白宣布对我和杨克明实行隔离审查。随即,清查组派来两个人进驻我的房间,实行24小时的监视。外出打开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当然更不准回家。
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该交代的问题均已和盘托出,再也写不出什么新内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虑此事,自学起英语来。
后来,为我建立了一个专案组。尽管特地为我的专案组调进新人,增强兵力,软硬兼施不断地审问我,但对我这个“堡垒”仍难以攻克,无甚收获。此时,北大历史系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审楼内,贴出一墙大字报,洋洋数千言,对我进行全面系统的“揭发和剖析”,与专案组内外呼应。
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北大师生员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32个单位的代表。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少说也在万人以上。首都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传中戏称其弟为兄建造了“耻辱柱”与“审判台”。
中午,“梁效”全体成员先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然后,大会组织者下令,从中挑出15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荣占首席,第二名是钟哲民,后边如何排列,难道其详,因为禁止我们东张西望。乐黛云在其自传中说,发现她的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这15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组长以上成员,外加我们写作小组的两名成员何芳川和陈先达。进入体育馆会场后,我们15名“梁效”骨干低着头,排成一字形站在体育馆中央示众。据说,台上还站着迟群、谢静宜、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是对我——“梁效”骨干分子,作为从严发落的典型,进行批斗。1977年12月31日《新北大》校报报道:“×××同志严厉批判了范达人卖身投靠‘四人帮’,炮制大量反党黑文,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并鉴于范达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实际情况,强烈要求从严处理。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坚决支持。”
随后,党委副书记韦明代表校党委宣布决定:“范达人在隔离审查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反党阴谋活动,经北京市委批准,决定范达人由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此次大会还宣布对一名“梁效”成员从宽处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到“梁效”没有几天,专做诗词注释,没有任何问题,将他作为从宽对象,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样,这次万人大会,又称之为体现党的政策的宽严大会。
宽严决定宣布后,就在万人大会上,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在许多学校和各界代表面前,我被公安人员押解出会场,上了一辆囚车。此时,车内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专案组长。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抬头向车窗外张望,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车内地板上。约半小时后,囚车在一座旧式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大门传达室值班人员首先收缴了我的手表、钥匙、人民币和粮票等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领着我往里走。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阴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进入一个过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询问值班人员,究竟将关在哪个号子。此时,一名剃着光头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号子前,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半步桥监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声,弄清了自己到了何处。
在狱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聂元梓。此时的她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昔日“光采”荡然无存。我从牢门的小孔中,还看见过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头,时不时与牢卒争吵。看到狱中有这么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丧情绪稍稍减缓,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监狱里呆了一年零十九天后,1979年1月17日下午,我走出了大墙,结束了牢狱生活。
我出狱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对我进行系统揭发和批斗的×××当面向我表示歉意。据说,当时北大党委要历史系出一人在大会上发言,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找到了他。这位发言者到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认为现在材料不过硬,不足以说明我问题的性质,而党委领导却鼓动他:“这事由党委负责,你就这样发言吧!”
说到当时的北大党委,我想到一位副书记,他原是中央团校负责人,后调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长,粉碎“四人帮”后,负责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极力按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基调,向我们施加压力,令我们老实交代。一次在俄文楼召开的对“梁效”成员训话会上,他厉声吼道:“范达人,你那篇文章(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如果贴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抓起来!”后来又在一次会上,他指责我们歪曲历史,说什么“史书上明明记载拥护武则天的人只有八千,你们为什么要写六万人?”当时,我心想是你把史实记错了。对他的训斥,我均沉默以对。
1979年,我出狱后,曾为我问题的性质一事找过他,一进客厅,见他正在阅读《资治通鉴》。他看到我,显得非常热情,说了一番颇为通情达理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华,进入“梁效”是由当时的组织上调去的,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发挥作用。
若干年后,他已到中央某一单位任职,一次游览长城时,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期而遇,当得知其中有我的儿子时,态度十分亲切。这位副书记对“梁效”成员的态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全文完)
上一页内容:
一、工字厅会议;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三、“梁效”的内部架构; 四、一段清闲
五、评《水浒》
【相关链接】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