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本站评论>应学俊:简论客观真实的“中国模式” P.1. | | 您好!今天是: | |
 |
|
简论客观真实的“中国模式”· 应学俊 ·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续博客点击数: 人次) |
|
中国用30多年时间实现了“崛起”,严格地说主要是经济腾飞,举世瞩目,这是事实。尽管前苏联和更早些的希特勒德国也曾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过非常了得的“崛起”,也曾搅动世界,但中国的和平崛起似乎更令世人瞩目和称道,这不可抹杀和无视。同一执政党,同一基本政治体制架构,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前30年”跌跌撞撞,失误不断,“后30年”却神奇起飞,这其中自有道理,自有其经验和逻辑——概括起来则被称为“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也有人认为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但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显示,还是有一种“中国模式”存在的。因为,所谓“模式”,按一般定义来讲,就是指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某种较稳定运行的“范式”。那么,中国近30年的发展,是大体存在这样一种“模式”的——现在,官方称之为“中国方案”或“中国智慧”。
有关“中国模式”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各有长短,有一些也不乏独到之处。但本文拟从另一视角,兼顾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做一点通俗而客观的探讨。
其实,“中国模式”或曰“中国方案”,实事求是概括起来非常简单,即:一党绝对领导,构成强势政府,有限市场经济,给予低级民主(主要在经济领域),严密管控社会。这便是客观真实的“中国模式”或曰“中国方案”。也有专家更加言简意赅:所谓“中国模式”即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管制(全控)市场经济。是一种难以复制和长久持续的模式。(见:王建国教授演讲视频)
在这样的模式中,“一党绝对领导、构成强势政府”、“严密管控社会”是承继“前30年”并未改变的;唯上述“有限市场经济”和“给予低级民主”是对“前30年”的否定或改变——正是这两项改变,与中国迅速“崛起”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但可否持续,还有待论证和检验;而有专家已经论争:无法长久持续。如此而已。这样的“中国模式(方案)”其操作方式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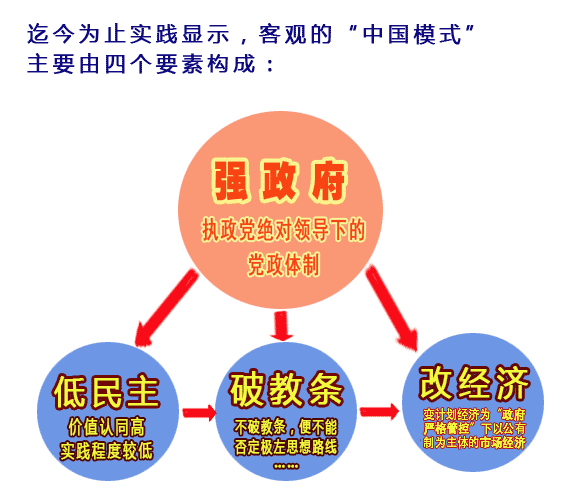
张维为以“中国崛起”的事实为论据,概括“中国模式”为“一国四方”,笔者不敢苟同,总感觉难避隔靴搔痒,未触及真正导致“中国崛起”的“中国模式”之实质,因为“一国四方”中所列大多要素,与“中国崛起”这件事并非存在必然的、排它的因果联系。笔者曾有专文《点评张维为的“一国四方”论》,在此不赘。
笔者在这里将排除“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尊重事实,以事实和逻辑为依据,试概括依然“在路上”的“中国模式”——并非为其背书、立言,或者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国模式”的目的,是依据事实,揭示本质,既从中总结经验,也总结教训,更重要的是必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利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规律”永远大于任何“主义”和教条。
任何理论皆源于实践。概括“中国模式”,必须基于改革开放发生、发展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先在头脑中形成某些想要阐发的观念,然后根据主观需要去“搜寻事实”,这样做往往跑偏而不自知,自然也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现象与本质是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重要的方法论。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客观上按照以上四个要素操作,不仅直接导致“中国崛起”,而且有着内在先后的逻辑联系,因果关系显然,且大多具有排它性(即“有A才有B;没有A便不会有B”);而若论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弊端和发展瓶颈,也同样与这些因素有着或大或小的因果关系。“中国模式”或曰“中国方案”——其合理优势与失误弊端及经验与教训并存。合理优势导致成功,失误弊端导致问题和发展瓶颈,皆有其逻辑和规律。下面简要阐述。
1.“强政府”——并非中国崛起的因素
所谓“强政府”并非仅指政府,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即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强势党政体制。2017年3月6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点击引文出处)。2016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对党政一体之“强政府”的最好诠释;改革过程中一度推行的“党政分开”客观上已被否定——尤其到2017年。
这里的“强政府”亦可借用萧功秦教授之说,即所谓“威权政治体制”。
“强政府”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崛起”有没有作用?肯定有。对于一个大国的改革大业,对于一个八亿国人大脑曾被禁锢30年并灌输了许多错误理念的大国,对于要触动某些人或阶层既得利益的改革,启动初始——犹如汽车发动之初,必须有强力推进、排除干扰,绕过纷争,才能得以开动;先干起来再说,“摸着石头过河”,一个行动有时胜过一打纲领。这就是“强政府”或曰“威权政治体制”在推动改革“上路”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但是,尽管如此,从事实和逻辑来看,“强政府”并不能成为“中国崛起”必然的、不排它因素——因为,自1949年以后这样的“强政府”就一直存在,并非改革开放才有。而就在如此“强政府”体制下,“前30年”中国某些方面虽也有所发展,但不仅算不上“崛起”,反而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决策失误,酿成重大挫折和灾难,以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后于港台、韩日新加坡几个亚洲蕞尔“小龙”。“前30年”历史并不过于久远,起码年近花甲及以上的普通国人都还记忆犹新,故无须赘述;若细述,那是另一篇文章了。既然“有A未必一定有B”,那么,“强政府”之与“中国崛起”的关系,从事实和逻辑上讲就不是必然因果关系——而只能说,这个“强政府”在“后30年”“做对了”一些事。(“做对了”哪些事,笔者曾有专文论及,见文末)。
“强政府”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尽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列车启动并较稳定运行后,一不小心它也会成为“双刃剑”。这时的“强政府”也会产生负面作用而影响改革与继续发展。
道理、逻辑和事实都很显然:“强”与“弱”必是相对存在的。既然有政府的“强”,就必然会带来民间力量的相对“弱”;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在“强政府”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民间力量自然会受到抑制和束缚。在“摸石头”发展中,“强政府”难免会越过应有边界,客观上侵犯公民及某些公民团体的权益——在司法不能真正独立的前提下,法治的客观、中立、公平、公正、依法规范社会、官民行为的作用便不能充分彰显,媒体监督也受到“强政府”的约束,公民和公民团体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及应得利益会因此受损,公平正义缺失,积极性受挫,正当行为受阻,民心就会离散,就会影响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提高——这些尽管并非“强政府”主观愿望所致,但客观效果的确如此。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何摆正“强政府”在中国继续发展中的位置,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强政府”之“强”对民间之“弱”的抑制是矛盾的——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崛起(邓小平称之为“松绑”)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强政府”在办成一些“大事”的同时,又必然削弱了很重要的民间助力国家“崛起”的积极性和能量。人民毕竟是国家、社会的主体,他们不断受到抑制,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会产生动摇,
这就是“强政府”之与“中国崛起”二者关系的逻辑与辩证。“党政府”之强,“前后30年”都一样,故它不可能是“中国崛起”的因素。从某个角度而言,是否可以借用俗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低民主”——这才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但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这里所说民主,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对民主价值认同和程序实践两个层面来说的。具体而言,则是价值认同颇“高”;但在民主的实践层面,尽管有所改革、推进和提高,但总体依然偏“低”。
对于民主核心价值,“后30年”中国官方对此认同度和宣示并不“低”——无论从《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第三十五条所赋予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而言,无论从《物权法》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以及一再宣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言,无论从领导人宣示“人民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而言,还是从将“民主”列入国家推广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已经很不低了。201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书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篇章》,2016年3月17日的社论则是《以民主凝聚人心力量 以法治护航改革发展》。
而所谓民主在程序和实践层面的偏“低”,则须从两个层面论述:其一,这样相对于“前30年”也算稀缺的“低民主”,在中国发展和“崛起”中不可替代的“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其二,这样的“低民主”所产生的发展中的问题。
不论是“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好,还是观念上还存在障碍也罢,在实践层面,中国的确是“低民主”的。
⑴ 实践层面“低民主”的表现和原因:
毋庸讳言,官方对“特色民主”另有界定,所以在民主的程序实践层面,其程度还是很“低”。笔者并非简单认为“一人一票选总统”就算民主程度高,而现实是,当前《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另行解释、界定和立法,实践中“强政府”往往以强视弱,并不能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使公民原本应当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和“缩水”。公民在经济、政治两个层面的民主程度呈前略高后极低状。但客观规律和逻辑、事实告诉我们,若没有政治层面的民主保障,经济层面的民主也随时会发生客观上的扭曲和限制——所以,实际上民主程度总体还是低的。若详细论证,又将是一大篇文章了,好在国人都明白,无须细述。
民主的实践程度偏低,有《宪法》规定、官方界定与实践操作无法统一的问题——笔者借用近几年官方推崇的“理论明星”宋鲁郑的话来说——也免费笔者笔墨:“中国目前这套理论体系,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表述上。虽然从宪法上讲,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各级党委常委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所以,以我的观察,中国现在的话语体系不仅无法说服党内,也无法说服党外,国内无法自圆其说,国外也同样无法被认可。”宋鲁郑还明确认为:“这个话语体系某种程度缺乏现实操作性,或者与现实不符”。(以上引文见宋鲁郑《跳出西方框架,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从〈中国超越〉谈当代政治理论创新》)。宋鲁郑这里倒是实话实说,也算一步到位,无须笔者另做说明了。
笔者要说说明的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这样的“低民主”固然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值得维持的因素——因为,正是这样的低民主,导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起飞的同时,产生了很多问题,阻碍继续发展,邓小平形象地概括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什么?自然不是骂生活有所改善(即所谓“吃肉”),而是如下一些方面:
比如,司法不公、违法执法、刑讯逼供或权大于法;
比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特权人物疯狂聚敛财富不受监管肆意妄为堪比“窃国”;
比如,土地财政导致房价一路飙升无法遏止,征地上市后政府所得高于给付农民补偿的百倍或更高,失地农民利益受到较大侵害;
比如,政府强拆强征不断酿成事件,此起彼伏(可点击),媒体很少获准报道;
比如,表达诉求上访难,迫害上访人,甚至上法院打行政诉讼官司也被整车押回,名曰“维稳”等等;
比如,百姓揭露官员腐败行为风险极高,媒体更不能主动“扒粪”监督;
比如,某些选举形同虚设或弄虚作假,法律规定的公民联名公推人大代表候选人无法实现;
 比如,民生问题固然重要,但“两会”几乎全让经济问题或所谓“民生”问题覆盖,政治问题无人敢于提及,有些具体事件、事项成了“禁区”等等……
比如,民生问题固然重要,但“两会”几乎全让经济问题或所谓“民生”问题覆盖,政治问题无人敢于提及,有些具体事件、事项成了“禁区”等等……
这些就无法不让老百姓“骂娘”了。经济上的民主,必须有政治上的民主为保障,否则就成了跛足,想“稳”也不得。这是违反逻辑和规律的。可以说,许多问题正是“低民主”造成的。
⑵ 即便这样的“低民主”(加上官方对民主核心价值的高认可),也是“中国崛起”牵一发动全身的因素。因为即便这样的“低民主”在“前30年”也是极其稀缺的。
(未完,接下页)
【参考文献 · 延伸阅读】
| (本站 2017-03-05 编辑转发 / 2020-05-12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