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陋室文化>应天常教授专栏>“去主持人化”是一个伪命题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本站其它链接
“去主持人化”是一个伪命题 |
■ 应天常(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 撰稿:应天常 信息源:作者赐稿 / 另见《南方电视学刊》2016年第3期 本站编辑转发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现在网络主播(主持人)大量出现,值得关注和研究。所谓网络主播,是指互联网中一档节目或播出单元从策划、编辑、录制、制作、观众互动等一系列工作的主持人。它现在已成为一种综合能力很强的职业。据了解“网络主播”的资格由中国主播行业协会官方认证,并颁发主播资格等级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级四个等级。一个优秀的网络主播常常要面对线上数万人、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观众,据山东广播电视台《小溪办事》报道,山东临沂一位18 岁的知名主播,拥有50 万粉丝,在4个月时间里盈利14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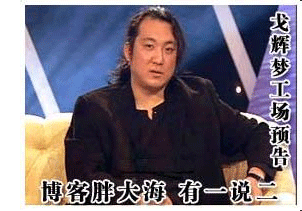 此外还有播客(broadcast)的出现也不可小觑,它其实是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电台或电视台。北京一位名叫胖大海的播客,通过一些搞笑视频或评论爆红,凤凰卫视和湖南卫视都做过报道。
此外还有播客(broadcast)的出现也不可小觑,它其实是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电台或电视台。北京一位名叫胖大海的播客,通过一些搞笑视频或评论爆红,凤凰卫视和湖南卫视都做过报道。
由此可见,网络视频节目兴起,不是“去主持人化”的催化剂,恰恰相反,它是主持人“泛化”、“多元”的催化剂。
三、《超级女声》等真人秀节目并未“去主持人化”
该文作者在阐述“去主持人化”的演化过程时指出:2005 年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评委’和主持人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后来“评委”进化为“导师”,于是“主持人已经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直到2013 年选秀节目风靡荧屏,“这场热闹竟然与主持人无关了”。而且 “2015 年仍有延续之势”,是“迅疾而来的变化”。
但是,恰恰相反,在笔者眼中,这是中国主持人节目理论和实践的进步,而且,在这些节目里,主持人是无处不在的。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厘清“节目主持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节目主持人是在大众传播活动的特定节目情境中,以真实的个人身份和交谈性言语交际行为,通过直接平等的交流方式主导、推动节目进程、体现节目意图的人。”(见拙作《节目主持人通论》2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这个概念界定,包括张君昌先生在内的业界学界朋友是认同的。以此观之,《超级女声》中的“评委”“导师”都可以看作是节目主持人。《开心辞典》里王小丫不既是评委也是主持人吗?包括该文作者后面论述中提到的“嘉宾”都可以看作是没有挂名的“节目主持人”。因为他们都在特定的节目情境中,以真实的个人身份和交谈性言语行为,共同主导、推动节目进程、体现了节目的意图。比如《非诚勿扰》里的黄菡老师,这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作为孟非的助手,也很好地发挥了主持人功能,只不过我们给了她“嘉宾”的头衔罢了。
这个概念界定,包括张君昌先生在内的业界学界朋友是认同的。以此观之,《超级女声》中的“评委”“导师”都可以看作是节目主持人。《开心辞典》里王小丫不既是评委也是主持人吗?包括该文作者后面论述中提到的“嘉宾”都可以看作是没有挂名的“节目主持人”。因为他们都在特定的节目情境中,以真实的个人身份和交谈性言语行为,共同主导、推动节目进程、体现了节目的意图。比如《非诚勿扰》里的黄菡老师,这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作为孟非的助手,也很好地发挥了主持人功能,只不过我们给了她“嘉宾”的头衔罢了。
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比较狭窄,可能与理论“库存”比较贫乏有关。为了说清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世界广播电视史。
“节目主持人”是舶来品,最早设置这个媒介角色的是美国,唐•休伊特定名为“Anchor”. 而在美国,主持人率先亮相是在娱乐选秀节目中,比如弥尔顿•伯尔乐(Milton Berle)于1948年创办主持的《德克萨克明星剧院》、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主持的杂耍节目《城中大受欢迎的人》热播16年之久;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推出的阿瑟•戈弗雷主持的《天才展现》、英国BBC推出的《百万富翁》……这些节目中出现了“Moderator”式主持人。
“Moderator”意为“协调人”、“仲裁人”,是美、英等国娱乐、选秀类节目主持人的称呼。从节目内容的选择、节目基调的确定、节目形式的设计、气氛的营造和进程的操控等方面看,他们都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同我国出现的类似选秀节目中的“评委”、“导师”、“嘉宾”所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节目的“协调人”、“仲裁人”。
由此看来,在我国的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不是作者所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是以另一种冠名形式一直存在的。
四、“去主持人化”可能是作者的愤激之词
广播电视的播出始终存在一种“界面人物”。所谓“界面”是指不同物体的接触面,广播电视的“界面人物”是指在节目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进行联系和交流的中介人。这个人可以是播音员,可以是主持人,包括现场记者,不可或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为什么作者要提出“去主持人化”这个命题呢?
显然,该文作者提出“去主持人化”也没有完全的把握:第一,作者把它放在“极简选择” 的层面,强调只是一种“临时应变”的策略性选择,并不真的要“去主持人化”;第二,作者不避“悖论”之嫌,在文末一再强调:“电视节目不可能完全‘去主持人’,因为一个媒体必须有属于自己个性的声音……”。
既如此,作者为什么要写一篇“去主持人化”的文章呢?
通读全文,笔者发现此文除了立论有误、阐述不周以外,还隐隐感到作者的某种专业焦虑和愤激。
作者指出:现在的主持人“只靠字正腔圆和少得可怜的思想和见识实在难以征服众人心”,因此“观众会毫无痛感地舍弃主持人”……
由此看来,所谓“去主持人化”可能是特有所指的。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而且,境况之严峻不止于此。
记得有一篇随笔,这样描述这些主持人现象:“也不知从哪年起,当我们看腻了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老化主持人,渴盼着充满活力、贴近观众的‘新型’主持人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却一下子又被一大群花花绿绿、手舞足蹈的形象所充斥。这些形象一律有着机关枪般的语速,小儿多动症般的手势,港台艺人般的语气语调,以及对节目主题内容丝毫没有深入了解的肤浅……”(方红:《谈电视节目主持人风格之抄袭》,载《现代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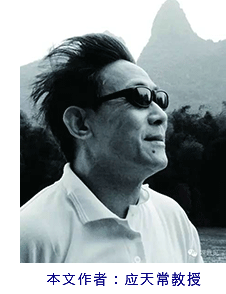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去主持人化”这个命题不能成立,但文章的某些内容还是含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去主持人化”这个命题不能成立,但文章的某些内容还是含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自媒体时代,新技术在社会转型时期对电视节目的强势介入,使原有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发生动摇,节目主持人的功能、形态、操作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拓展,当网络主播、网络播客把节目主持得风生水起,点击量不断攀升,我们能适应这样的媒介秩序吗?我们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和专业实力同他们分庭抗礼吗?这确实是我们的新闻教育和在职节目主持人无可回避的课题。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相关链接】
▲ 谷岩 胡哲:“去主持人化”——网络时代电视节目的极简选择
▲ 杨澜,还是别这么说——关于《主持无艺术》的对话(应天常、陶曼)
▲ 应天常:“官方舆论场”质疑——兼与人民网总裁廖玒、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商榷
(2016年8月编辑发布 / 2019-03-06 更新)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