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首页>教育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选载:13.文本与对话:教学规范的转型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钟启泉教授 |
课改实践探讨:
| 点击图片,到本专辑目录: |
 |
| 点击:到“教育理论”栏目… |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 |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
13. 文本与对话:教学规范的转型 |
| 主编:钟启泉、崔允漷、张华; 主审:朱慕菊 |
| 主编:钟启泉、崔允漷、张华 主审:朱慕菊 来源:本书 本站 2006年9月 编辑发布 |
【本站按】本文选自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主编、朱慕菊/主审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文章从分析揭示教学的本质入手,阐述和论证了教学规范的“转型”问题。分三部分阐述:一、教学:“沟通”与“合作”的活动(侧重理论);二、“教材”与“教学”概念的重构;三、教学规范的转型。(可点击小标题选择浏览) |
| (点击这里:承前页) |
二、文本与对话:“教材”与“教学”概念的重建 (点击这里:承前页)
将教学主要理解为语言性沟通或语言性活动,是研究教学现象的本质的一个前提。这意味着进一步提高了对于教学之媒体——教学语言——的关注。克林伯格指出,“在所有的教学之中,进行着最广义的‘对话’。……不管哪一种教学方式占支配地位,这种相互作用的对话是优秀教学的一种本质性的标识。”④ 在他看来,教学原本就是形形色色的对话,拥有对话的性格。这就是“教学对话原理”。
教学“对话”(dialogue)的过程有可能用到“文本”(text)的概念。而对文本的理解需要从“文本生产、文本、文本接受”的整个过程来把握。
教学活动中的文本,有其特殊的情境性和独特性,因此,这里所说的文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而是教学的文本。教学文本是在教学沟通的过程中生产和接受的,可以视为会话文本与读写文本,以及对话文本与独白文本的总体。⑤ 这种教学文本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合作创造的极其复杂的产物。目前来看,尽管人们对教学文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文本有助于推动教学的功能机制与教学设计原理的研究,并对教学的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就后者来说,对教学语言具有影响作用的文本主要有:
1、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或是咨询报告之类的文本。
2、“学科课程标准”所代表的赋予学校教学以方向的教育政策文本。
3、“教学指导书”所代表的赋予教师的教学活动以方向的文本。
4、提供教学内容的科学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文本。
5、以“教科书”与“教材”为代表的经过教学论加工的专业文本。
6、以电视、录像、广播为代表的一定媒体结合的视听文本。
7、以“教案”为代表的沟通策略与沟通计划——教师的教学设计文本
8、教学设计中教师所准备的提问与问题设定之类的教师的语言行为。
9、学生作业、考察报告之类的学生预先准备好的语言行为。
10、教学中教师的语言操作。
11、教学中学生的语言操作。
12、教学结束后所产生的文本。例如:教师的教学记录、学生的作文等等。
我们可以从教师的教学活动——计划(P)、实施(D)、评价(S)——的角度对上述文本进行分类。分类后的文本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教师并不直接参与制作的、现成的文本,相当于前述的1-6。
第二,教师事先准备好的教学设计文本,相当于前述的7。这是教师根据前述的文本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状态编制的教学计划。设计的教学文本同实施的教学文本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落差,考察两者间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三,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创造的文本,相当于前述的8-11。这种教学过程中的文本有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于现成文献形式的文本,能够形成教学的媒介过程与习得过程基础的文本,诸如教科书文本、资料文本、学生所生产的报告文本、练习文本、同种媒体结合的文本;另一种是在教学沟通过程中所生产的种种文本,诸如板书、教授、对话、讨论、笔记、摘要乃至对学生的操作活动进行的激励和发出的指令。
教学以第一种文本为基础,并在第二种文本的创作中变革的一种文本,从而形成新的沟通产物。这两种文本的结合生成了教学内容。因此,教学内容是在教学过程之中创造的。
第四,教学告一段落后教师和学生所生产的文本,相当于前述的12。在这一过程中也生产同第一类相关的文本,例如,教师通过对教学实践(授课实录)进行分析所生产的文本。
把教学语言作为教学文本来把握,开辟了考察教学理论的一个崭新领域。这种教学文本是在动态中形成的,它的生产者与接受者既是学生,同时也是教师。不过,这种动态性的教学文本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教育教学环境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分析这些条件与文本生产和接受的关系也是本文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我国“教学文本”的生产与接受的实际运作来看,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亟待研究——
第一个问题,“教材”概念的广义界定及其编制
教学是由种种要素构成的极其复杂的动力性过程,教学的结构通常由三大要素构成——教师、学生、教材(教学媒体)。这种界定可以说是自赫尔巴特以来人们把握教学结构的最经典的模型。也就是说,教学必须包容教师、学生以及共同处置的“第三者”——教材,没有“第三者”介入的教学是不可思议的。不过,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的“教材”的内涵却有着多歧义的特性。尽管如此,关于教材最普遍的、广义的定义是,“教材”是教师在教授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了最标准的教科书,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图书教材、视听教材、电子教材等。其中,教科书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教材;换言之,“教材”的概念囊括了作为核心教材的“教科书”。教科书的改革不外乎采取两种策略:或是量的删繁就简,或是质的结构性改革。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国每一轮的课程教材改革大都囿于从量的侧面去考虑改革策略,认为旧有的学科及其内容是天经地义的;认为“厚本变薄本”可以收到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效果,甚至把减轻书包重量等同于减轻学业负担。然而,书包重量未必意味着学业负担重。这是因为,构成学业负担的要素主要取决于每个学生的“认知结构”水准和“学习动机”水准。从主观方面来说,面对经过主观努力能够达成的某种目标,那些既有适当认知结构又有较强学习动机的学生,即使背着再重的书包也不会感到“沉重”;相反,对于那些毫无学习兴趣且认知结构低下的学生来说,即使书包里仅有薄薄的一本书他们也会感到“不堪重负”。从客观方面来说,素材丰富、有血有肉的教材远比成人化、教条式的枯燥呆板的教材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教科书的编制需要有一系列的智力操作和技术手段作为准备。
希尔斯(Hirsch,E.D.)从“文化素养”的观点引出的“核心知识”与“核心知识课程”概念值得我们借鉴。⑥ 波依尔指出,基础学校在考虑学科设置之前必须就“核心知识”作出界定。所谓“核心知识”是指所有的人拥有的普遍经验和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的人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⑦ 这里面包括:“生命周期”、“符号使用”、“集体成员”、“时空意识”、“审美反应”、“天人相依”、“生产消费”、“高尚生存”等。这八种“核心知识”实际上反映了它们在人生旅程中的顺序。首先,“生命周期”始于人的诞生之日,接着是语言(“符号使用”).然后,小孩子从家庭开始认识自己是各种“集体”中的一员。他们很快会有“时空意识”。儿童们对美好的事物作出“反应”,并且逐步地了解食物从哪里来,认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联”。待其进一步成熟之后便开始学习如何制作并使用工具,儿童们自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这八种基于人类共同经验的“核心知识”有助于整合传统的科目,有助于学生理解种种学科知识所拥有的关联性,有助于学生把书本知识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波依尔认为,基础学校应当围绕这些核心知识设计学科和领域,渐次复杂地、螺旋式地展开,形成一贯统整的课程。在这种教育学的加工中,其实蕴含了“文化内容”、“教育内容”、“教材(教科书)”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⑧我们应当依据教育宗旨,首先从浩瀚的人类“文化内容”中精选出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知识,然后围绕核心知识收集、组织大量的素材,然后才谈得上“教材(教科书)”的编制工作。多年来,我们的课程教材改革工作缺乏对这种“文化内容—教育内容—教材(教科书)”的区分及对其运作程序的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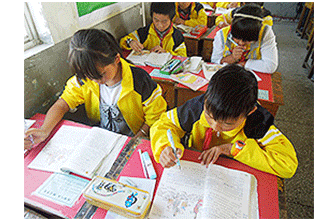 今天的教材改革实际上已经扩展为一整套教学媒体的开发、“教材”不仅限于教科书,围绕教科书的教学资料应当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教学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于一线的教师。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一般受到国家的直接控制,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格与历史性格,具有经过专家审定和行政认可的权威性。不过,开发形形色色的教材则是属于教师专业范围的课题。
今天的教材改革实际上已经扩展为一整套教学媒体的开发、“教材”不仅限于教科书,围绕教科书的教学资料应当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教学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于一线的教师。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一般受到国家的直接控制,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格与历史性格,具有经过专家审定和行政认可的权威性。不过,开发形形色色的教材则是属于教师专业范围的课题。
如何使用教材(教科书)——是“教教科书”还是“用教科书教”,这是区分教师专业化程度的标尺。⑨“教教科书”是传统的“教书匠”的体征,“用教科书教”才是现代教师应有的姿态。
因此,教科书仅仅是众多教学媒体中的一种。更何况,今天的教学环境正在发生反天覆地的变革,凭借网络系统支撑的庞大的知识世界,为师生不断去界定和在界定文本以及不断发现意义,提供了无可限量的资源。“教材”不是单纯的“知识点”的代名词。
教材作为一定学科(或领域)的载体具有两种基本特质:其一是“典型性”。学生是通过教材习得学科内容的,教材必须是学科内容的全面、稳定、序列、准确的载体;其二是“具体性”。教材是学生旨在习得一定学科内容而直接分析、操作、综合的对象,教材必须确凿、具体,并有助于引导学生展开智力活动。
从本质上说,“教材”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
一、作为学生的知识体系所计划的事实、概念、法则、理论;
二、同知识紧密相关,有助于各种能力与熟练技巧的系统掌握、心理作业与实践作业的各种步骤、作业方法与技术;
三、知识体系与能力体系的密切结合,奠定世界观之基础的、表现为信念的、政治的、世界观的、道德的认识、观念及规范。⑩
传统的教材观把教材仅仅限于事实性知识,或者原理性知识(概念、法则),而忽略了能力体系以及思考方式、伦理道德信念。新的教材观突出了方法论知识和伦理性知识。单纯围绕“知识点”的说教式的教材设计是片面的,是背离“素质教育”要求的。
第二个问题,教学环境的“信息化”与“生活化”
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或是“知识移植”的过程。如前所述,真正的教学过程应当说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
然而20 世纪的教学形态可以说是以“教室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为特征的。这是一种适于教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教学形态,即“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教师的作用只是牢牢地控制住学生,传授现成的书本知识。21 世纪的新型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是培养学生在未来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并为此设计、组织相应的使学生成为学习活动主体的应答性的学习环境。这意味着未来的教学模式将从“人←→人(man-to-man)”系统,转变为“人←→环境(man-to-environment)”系统。⑾
以“三中心”为特征的课堂教学系统谓之“人—人”系统。前面的“人”是教师,此“人”通过“口授”将知识技能传授给后面的“人”——学生。在这个系统里,靠一名教师的能力对数十名学生同步施教,在现成知识的授受上是极其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学生却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在这里,学生仅仅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不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要使学生成为自主知识的“习得者”,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系统,这种新系统便是“人—应答性学习环境”的系统,这里的“人”是指学生。要保障主体性的学习活动,就得使学生直面应答性的学习环境。这样,学生就会直接地作用于这种应答性环境,解决自己的学习课题。可以说,这是一种学生主动参与的、尊重学生个性的、参与型教学环境。在这里,教室和教师并非学习环境的全部,课堂教学也不再限于传授的教科书、黑板、粉笔之类的媒体,而是有了媒体系统乃至因特网的支撑。可以相信,今后的教学将会受到丰富多样的媒体与人力的支持,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活动场所。
(未完.点击下一节:教学规范的转型)
【注 释】
④ 克林伯格著:《社会主义学校(学派)的教学指导性与主动性》,德国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 86页。 ⑤、
⑿ 木下百合子著:《教学沟通与教学语言之研究》,风间书房平成8年,第143、186、181页。
⑥ 参见高文主编:《现代教学的模式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章。
⑦ 波依尔著,中岛章夫主译:《基础学校》,玉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31页。
⑧ 奥田真丈等主编:《现代学校教育大事典》,行政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及348—350页。
⑨ 吉本均主编:《现代授业研究大事典》明治图书馆1987年版,第80页。
⑩ ⒀ 钟启权编译:《现代学科教学论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38页。
⑾ 加藤幸次等主编:《学习环境的创造》,教育开发研究所1997年版,第11—12页。
![]() 返 回:解读《纲要》选载 · 目录页
返 回:解读《纲要》选载 · 目录页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06-09-02 编辑发布 / 2018-11-30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