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历史钩沉>新中国文坛第一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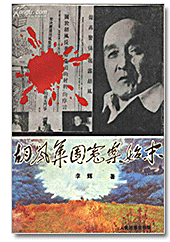 |
|
★ 本站时政评论目录
点击:到历史钩沉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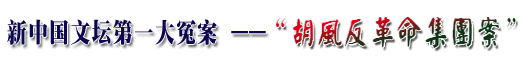 |
| (中国文坛网 / 2004-09-13) |
| 来源:中国文坛网(2004-09-13) 作者:文坛采编 责任编辑:文坛总编 本站编辑转载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
||||||
● 两个口号之争
胡风和鲁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与其他几个“左联”负责人之间却有误解和矛盾。后来一切问题的症结,都起源于此。
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讲到当时“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曾告诉他,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请他注意。
鲁迅不以为然,并为此对周扬等有反感。“胡风鲠直,容易招怨,但是可以接近的”;他认为胡风的缺点是:“神经质,繁琐,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不肯大众化”;但“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认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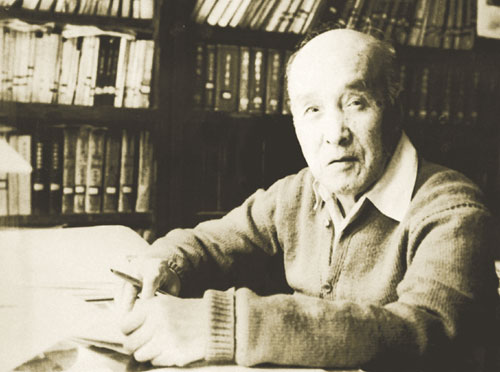 1936 年夏,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问题争论。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由胡风在一篇文章公开提出。但胡风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个口号是经过鲁迅同意的,而且只字不提“国防文学”。
1936 年夏,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问题争论。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由胡风在一篇文章公开提出。但胡风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个口号是经过鲁迅同意的,而且只字不提“国防文学”。
因此,对胡风本就有看法的主张“国防文学”的“左联”成员,便认为胡风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而另提新口号,分明是蓄意标新立异。于是,批评了胡风提出的口号。
其实,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国防文学”意义不明确,而且有“右”的倾向,他们也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于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围绕着“两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在各自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坚持己见,批评对方。后来,因鲁迅的逝世和不久爆发的“西安事变”以及第二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才偃旗息鼓。
然而,文艺界的宗派成见和彼此间的积怨并没消除。胡风只写了一篇文章就退出了论争,但主张“国防文学”的不少人指责矛头是对着胡风,而不直接指向鲁迅。
抗战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他担任文协理事会的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这时胡风独立创办了《七月》杂志。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起到了良好作用。1941 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1938 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个指示使延安和重庆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重庆文化界讨论中,提出了“旧形式的利用”问题,即“旧瓶装新酒”,利用旧形式来表现抗日革命新内容。当时,向林冰就此提出了一个论点,说“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认为“五四”时兴起的各种革命新文艺只是“移植形式”,是从外国来的,不是民族的形式。向林冰的意见实际上全盘否定了因为受了外来进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新文化。
胡风不同意向林冰的观点,也不赞同和向林冰不一致的一些人的意见。1940 年10月至12月,他写了题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长篇论文。胡风特别强调外来文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并坚决捍卫这种新文艺的传统。“五四”新文艺接受了世界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方法和形式的影响,胡风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强调五四文学革命是正确的,但他的意见中也有一些偏颇。
在这次讨论中,胡风不仅是向林冰等人的“论敌”,而且与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文化界名人公开对垒。
他的正确观点没得到应有的肯定,反因理论上的偏颇之处,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对祖国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从而受到了长期的不公正的批判。
胡风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表示反感。
1941 年“皖南事变”后,为避开国民党的迫害,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在重庆、桂林的大批进步人士转移到香港。同年底,香港沦陷。1942 年3月,胡风回到桂林,组织了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文艺书刊。1943年3月,胡风又回到重庆。读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整风文献》,使他受到鼓舞,同时对《讲话》中的某些观点也有自己的理解。
【本站评注】这可就麻烦了。与文化沙皇、文化“帮闲”之巨头周扬、郭沫若等“对垒”,现在对毛的“讲话”还有“自己的理解”,这还了得?胡风拥护革命,拥护中共,为中共做过许多事情,但他似乎并不知道,在中共,是要“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必须做“党的螺丝钉”,要有“看齐意识”,要“保持一致”,岂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解”?即便有,又岂能表达出来?任何“宗派、地位、学术观点”之争,皆可假以“革命”的名义诛杀——这是胡风倒霉的全部原因所在。
文艺界的某些领导者根据《讲话》精神认为,当前主要应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要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
胡风则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状况及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认为当前应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
1945 年1月,胡风主编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胡风在《编后记》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
【本站评注】“主观”指人的意识、精神;“客观”指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或指认识的一切对象。即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而言,主观和客观也是对立的统一。“客观”是不依赖于主观而独立存在的,而“主观”则能动地反映客观,并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毛泽东也强调在社会实践中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此而已。
《希望》第1期出版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召开了小型座谈会,批评胡风及《希望》的思想倾向。胡风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表示反感。
《希望》第2期,又发表了舒芜的另一篇长篇论文《论中庸》。据胡风在《编后记》中说,本文是作者对《论主观》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
人们把舒芜的文章同延安整风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联系起来。
延安整风主要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而胡风主编的《希望》却宣传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这岂不是从思想根源上论证他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
1948 年,一批共产党员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相继发表了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林默涵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等文,点名批评胡风。
胡风没有被这些批评所说服,也没有马上反驳。
1948 年9月,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小册子,作为对批评者们的总答复。
在这本小册子里,胡风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深入批判了“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本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他们大多数是“劳动力出卖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传播先进思想的桥梁。胡风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些精辟见解,被认为是做了“知识分子的辩护人”,拒绝学习马列主义,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实际上,在这篇小册子中,胡风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以及知识分子作家思想改造和人民相结合的问题。【本站评注】胡风之论,何错之有?
这场论战的对方是邵荃麟、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人。
胡风说他“在着手之前,颇有踌躇,有过顾虑”。并一再声明,这些人都是他“所尊敬的友人”,希望这些讨论是“对事不对人”,请予谅解。
1949 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谈到了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他说,“主观”问题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中真正的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对胡风所持的文艺观点进行了反驳,成了后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基调。
● 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创作了大量讴歌党和人民的新诗。但是,胡风的作品要公开发表越来越困难。
1951 年9月24日至11月,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文艺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
1952 年3月,在整风运动领导机构出版的“内部通讯”中,发表了批评路翎在整风中公开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通讯。同时,《文艺报》向部分读者分发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小册子,要求读者发表意见。不久严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寄到编辑部。
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开始了。
1952 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的社论,指出:当前文艺界的问题,“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
胡风对此的感觉是“杀机似乎还有,但已不愿说得太明显了!”
然而,形势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1952 年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照《讲话》,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为自己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他还披露:“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
6 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舒芜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
“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
9 月25 日,舒芜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
舒芜的自责与揭露使胡风十分被动,他被莫名其妙地定为“资产阶级文艺集团”的头目,面临一场公开大批判。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要求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9 月6 日,“胡风文艺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
胡风先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大会要求胡风就“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 5 个问题做检查。周扬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 反党的路线。……最后胡风表示慢慢消化,努力学习,争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1953 年1月,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第二期《文艺报》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文章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2 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然而胡风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认为是断章取义。
【本站评注】胡风错了——你以为现在是那个对于某些学术理论问题可以自由争论的年代吗?你以为思想可以“无罪”吗?你认为“言者无罪”吗?——自然,无条件地服从并宣传坐在宝座上“圣上”的思想,肯定“言者无罪”啦。——几亿人有一个脑袋思考就行了,你胡风还能有什么“思想”?新中国建政,当局正要“统一”全国人的思想,正要树立毛思想的权威,你胡风正好撞在枪口上了。这时,可不管你曾多么拥护这个党.也不管你曾为这个党做过多少事情,你有不同的“思想”,就是异端邪说,必诛之。
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仅在文艺界,而且在整个社会激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这才批判高潮来临前的序曲。
● “三十万言书”
1954 年2月18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就高岗、饶漱石事件指出,党内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不但不接受批评监督,而且对批评者实行报复。
在胡风看来,文艺界的个别领导正是抱此态度对他进行批判。在深入学习了公报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后,胡风的一些顾虑基本解除,他决定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文艺界的个别领导展开斗争。
同年7月,胡风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共27 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
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及一封信。胡风在信中说明了自己上书的动机。
“三十万言书”共四个部分:
(一)进入解放区以来的经历与遭遇,指责周扬等人把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
(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中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就文艺领导、文学运动的方向、话剧运动的方式、电影剧本 4 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胡风“三十万言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第二部分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虽说胡风的措辞不无偏激之处,但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
● “五把理论刀子”
胡风进而提出了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这是遭到最严厉批判的论点。《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中有关“五把理论刀子”的几段原话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胡风将问题提得十分尖锐。胡风提出“五把理论刀子”,不过是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的一个形象比喻,但却被简单化为胡风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
【本站评注】如此指鹿为马在“反右”中再次上演,对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批判,与上述批判胡风的卑劣手段如出一辙。原本是说对读者和作者而言的“五把理论刀子”,却被硬说成是“指向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若真要坚持如此“指鹿为马”,那只能归结于胡风的概括“一针见血”?
● 批评《文艺报》
1954 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 8 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文艺报》负责人,说《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
本就对《文艺报》反感的胡风,认为这是批评《文艺报》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垄、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同时,胡风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十几个文艺界的负责人。
胡风的发言,引起了众多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发泄私愤。
【本站评注】大家的评论大约基本不错,胡风认为“机会来了”——好糊涂!胡风哪里知道,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文艺报》所谓“压制新生力量”的批判,包括对胡风的批判,后台老板皆为同一人,目的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尤其是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使他们俯首帖耳、为马首是瞻耳,今曰“看齐”。胡风此时“借机”,恰恰是“助纣为虐”了,怎不糊涂?在专制国家,受害者出于自保或报复害人者,也会成为施害者,这已成规律,“反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皆如此。这是制度文化的怪胎。
11月25日,文联作协主席团第6次扩大会议上,有人在发言中反驳了胡风。
12月8日,第8次扩大会议,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转入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在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一节专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从1953 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但毕竟只限于思想理论范围。
然而,事情愈来愈严重。胡风在听了袁水拍11月17日的反批评后,还没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劣势。胡风天真地错误估计了形势。
很快,《人民日报》12月16日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胡风才猛然醒悟自己的失策,开始意识到自己贸然出击,给想整治自己的人提供了良机。
● 一场永不可能取胜的战斗
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表,使鲁迅晚年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个朋友——冯雪峰与胡风一起被推入逆境。
胡风此时才真正醒悟,自己一直在打一场永不可能取胜的战斗。对方的力量如此之大,令他惶惑,令他惊奇。胡风原指望借助毛泽东对他的支持,把周扬等人击败,没想到形势变幻莫测,他射出的箭,返回来指向自己。他的苦心,他的计谋,简单而天真,他必须低头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与周扬对峙,他从不怕,但与他所由衷崇拜的毛泽东,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冲突,他也绝然不敢。一身硬骨的胡风,决定写检讨了。
然而,胡风内心矛盾重重,他不承认自己文艺观点是错误的,但又不得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他咬紧牙关,决定反省自己。 胡风的检讨是由路翎、绿原、欧阳庄等帮忙修改抄写的。
1955 年1月11日,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一开头,胡风便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
胡风在自我批评中,检查了自己在1940 年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导思想的论断,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与诊断;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片面强调实践,陷入了唯心论。但是,从文字当中,仍使人感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他尽可能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
对自己1949 年后的一些活动,胡风毫无保留地作了检讨。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05-07-12 编辑转发 / 2018-11-28 修订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