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历史钩沉>新中国文坛第一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P.4.)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 本站时政评论目录
点击:到历史钩沉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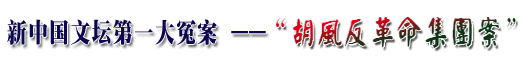 |
| (中国文坛网 / 2004-09-13) |
| 来源:中国文坛网(2004-09-13) 作者:文坛采编 责任编辑:文坛总编 本站编辑转载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
||||||
● 胡风、梅志:狱中患难与共
胡风被关押10年后,于1965 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监外执行。
1966 年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3 月,胡风刚和家人团聚 3 个月,就和梅志被遣送到四川雅安地区的芦山县的劳改茶场监督劳动,每月给生活费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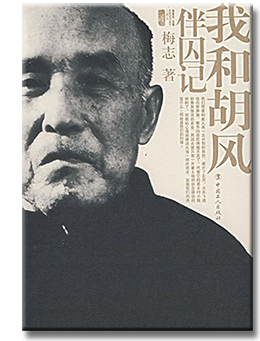 1967 年10月,随着浩劫的深入,胡风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和梅志分离。
1967 年10月,随着浩劫的深入,胡风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和梅志分离。
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胡风应于1969 年8月刑满,但对胡风的释放问题一直无人过问。
胡风于1970 年春,上书请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报告送出后,因为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无期徒刑,并将胡风押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其间,已出现了内因性精神病症状。
1973 年初,由于胡风病情变坏,经四川省公安厅允许,梅志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护理胡风。当梅志和胡风见面时,胡风已不认识她。这时的胡风完全处于幻听之中,但在梅志的精心照顾和精神上的体贴安慰下,胡风的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到恶化。
● 胡风最后一段狱中经历
梅志回忆:(为方便阅读,本站为这一部分加了小标题。梅志回忆以蓝色字体显示)
※ 1966年,“监外”仅3个月,又被遣送四川;短暂的“平静”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我们带着破碎的心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我们只感到了陌生和孤独。
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 3 年刑期。我的责任是照顾好他的身体,当然还得尽量使他过得愉快。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买了稿纸让他把狱中默吟的诗全部写了出来,又准备陪同他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他想写一本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美学方面的专著。不巧,图书馆正在整理内部,不对外开放。胡风抄完了诗,就由干事陪他去治疗多年积下的痼疾:耳鸣舌燥和痔疮。同时,也游玩了成都市内的一些名胜古迹。虽然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亲人,幸好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书,空闲下来就看看书,他的心情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身体也比出狱时好些了。我们开始对成都产生了好感,这里生活便宜,四季都有新鲜的青蔬菜,能在这里改造思想,修身养性,应该说是很幸运的。我们躲在这小院里,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这一点使得远在北京的老聂夫妇都十分羡慕,甚至于想来此与我们为邻。
其实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不久,报上就开始了批“三家村”的升级,连我们住的街上也经常召开批判会,贴上许多大字标语,很有点像1955 年批判我们时的架势。我们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毛主席又提出了“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的号召,看得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正在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又来催促胡风写思想汇报,并且要我尽快去文化局报到。
我盼望了十多年的工作机会,不得不放弃了。我想到,胡风好容易离开监狱来到了这里,我怎能让他受委屈?我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他身体复元,并完成他想写的作品,这要比我一天到晚呆在资料室里要有意义得多。因此,我再一次准备做他的助手,和他患难与共!
我们可以到城内各处去游览,也可以到街上去购买日用品。劳改局还派了一位干部陪着我们,做不是导游的导游。我们游武侯祠时,顺便在旁边的四川军人刘湘的墓地去参观,在那儿的一棵大铁树下照了合影。这高大的铁树,在别处可见不着。胡风说,这树有性格,它不以开花来逢迎游客。不过,我是希望看到铁树开花的。
※ “文革”被囚禁中仍须继续写交代
可惜好景不长。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三司”,他们在老皇城的大墙上贴出了“火烧省市委”的大字标语。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揪这打那地把我都搞糊涂了。×处长来通知:胡风不要再出门;就是我,最好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啊!”
但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皇城门口的那两个大红石狮子被人用铁锤砸了个粉碎。一个造反派还说:“吓,你这帝王将相的看门狗,我们就是要彻底把你打烂!”我还看到红卫兵将从上海来的妇女的烫发和小裤脚剪去。北京的小儿子来信了,他将不参加这次高考,并且从今后不和我们通信了。西安的大儿子也来信说今后不再和我们通信了,就只有当农业工人的女儿还给我们写信。显然,“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到各家各户了。
胡风的处境更糟了。他不断地写思想汇报,公安厅的负责同志还来找他谈,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19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地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
这些情况都使我非常为难,非常担心。除了劝解外,能尽力做到的只是买点他喜欢吃的菜,有时让他喝上一杯四川名酒解解闷,也算是享受生活吧。
到8月份时,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川省的党政领导多数成了走资派。大街小巷都被标语贴满了,戴红袖章的各战斗队杀气腾腾地,眼看形势将越来越激烈。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 突被遣送“苗溪茶场”· 中风倒地 · 与宿敌周扬成了“一丘之貉”
1966年9月初,得到通知要我们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为什么?到哪儿?没有一句话。但这是命令。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12点,那位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把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老冷坐在他的前面。这样,他就夹在了解放军和老冷之间。负责同志和司机坐在一起。
深夜的成都市,是静悄悄的,但是从大街一直到近郊区都不时有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骑着自行车匆匆地来来去去。
车子一直往前驶,可能已到了外县,那里连路灯也没有,我只能借着车灯的光亮看到路两边的情况。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
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和老冷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扑向司机,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这可不得了啦,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停在两傍高山的峡谷间,胡风由我和老冷搀扶着,好不容易才下了车,看来他已经憋得很难受了。这里是漆黑一团,连一块路牌都看不见,只能猜测这里是山区。峡谷的风很大,我感到了袭人的寒意,但胡风仍站在路边一动不动,大概是小便潴住了。我真怕他受凉,又不好催他,只有干着急。
好容易他才走过来,把他扶上车后,车又疾驰了。 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忽然,从路旁钻出一个人来,那突如其来的情况,真像是遭遇劫车大盗呢。但司机和负责同志却都和他打招呼,并且停下车让他上来。之后,一路就由他指引着,左拐右拐到了一处山下才叫我们下车。又由这位跳上车的干部(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个茶场的场长)打着手电筒引路,最后将我们引到了位于一个小山头上的一大间砖房里。这时,天已快亮了。
这里是四川省芦山县劳改局苗溪茶场。胡风当然是以犯人的身份送到这里来的,不过没有编入劳改队,还让我和他单独住在这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们的老冷。这儿四面环山,过去因这里庙宇多,本名庙溪。夏天各地的绅士地主们坐轿上山来这里避暑。现在改名为苗溪,那些庙宇已多半改为茶场办公的地方,四周的荒山也被开垦出来种茶和种果木了。
说好了让我们到一队(果园队)去打饭吃,优待我们吃小厨房的干部伙食,自己花钱买饭票。这样,吃的问题解决了。不过,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并且老叫头痛,情绪也非常不好。我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的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起先,我想这可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过些时日会慢慢好的。谁知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有精神,也没人问津。我想和他说点高兴的话,他只是向我摆手,还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这时,老冷才找来了医生。先是一个中年人,老冷说是院长。他看后说血压不正常,开了点药,但病人仍叫头痛、头晕。后来,又有一个中年医生和一个青年医生来看,说是有点感冒,并且血压仍不正常,开了点药,还叫我多给他喝水,最好是果汁。 我请老冷去城里给买些水果,他买了些梨来。梨个大而多汁,正好用它轧水。他心里有内热,嘴皮都是干的。梨汁他倒爱喝,只是仍不想吃东西,光喝点粥汤,人软弱得几乎坐不起来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说要大便,我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叫他别用力了,由我死劲拉了他起来,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他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简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着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多像希腊悲剧里受难者的雕像啊!可惜的是,当时我无法给他留下一张照片。此情此景,只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了。
第二天一早,我赶快将他的病情告诉了老冷,他反倒怪我怎么不早说。下午,弄来了一副竹制担架,由那青年医生陪着,说是送场部医院去。我拿着日用品在后面跟着。我们住进了两个人一间的干部病房,胡风仍是昏迷不醒。他们给我的任务是看着他,不让他跌下来。我就一直在他身旁。
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场长领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场长告诉我她是专区医院派来的。她给胡风做了仔细的检查,说是轻微的脑溢血加上受寒、消化不良。她打了一针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复诊,这时胡风已醒过来能说话了,他对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女医生对我说,没什么要紧,可能这两天会拉稀,要给他洗擦干净。又要我注意经常替他翻身,不要得褥疮,还有,千万不能让他跌跤,因为血压仍偏高。
只要是医生说的,我都照办。第3天,他能吃东西了。我就托老冷赶场时买了一只鸡炖汤下挂面给他吃,又吃了些鸡蛋、猪肝之类。第4天正好是国庆节,他竟然下床想听听北京天安门的实况广播。不知是离得太远了还是这里的收音机不好,只知道林彪在讲话,可一点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他一能下地,我就扶他出去晒晒太阳,也在院坝内走走。
院长看见了很高兴,就说是该出院了。我说,他还没有复原,住这么四五天就出院,能行吗?他说可以叫人给背回去。我和胡风听了都感到奇怪,一百三四十斤的老人让人背回去,我不放心。但看来又非走不可了。我就找了一根竹杖,扶着胡风在院内练习走路。幸好,发病时他没有倒地,手脚都没受影响,只是眼睛看不太清了。这没关系,我可以扶他走回去。
一两天后,院长就来通知说,天晴了,可以走了。并派了一个人为我们带路,还在一旁帮助胡风,以防在泥泞的路上滑倒。这里雨后的泥路很难走,像搽了油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跌跤。我只好踩着前人走过的脚印走,或者走在路边的草上。幸好我手里也拿了根竹杖。就这样,一步一滑地,我们总算平安到了“家”!
回到小屋后,使我们最感失望的是知道再也不能回成都了。这里已经成立了管理所,是专门管我们的。新所长来见了面,要胡风安心养病,暂时可以不写思想汇报。胡风提出想让我去成都取点书。他说,读3本《毛选》吧,要好好学习。书和其他东西,都会送来的。看来,我们将长住在这里了。
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山谷里一刮风就冷得很,而太阳底下却暖和得很,老乡们可以脱去棉衣,光着膀子捉虱子。我在北方住了十多年,对这种气候就很不习惯了,经常感冒咳嗽。胡风倒比我还能适应,没感冒,就是老说眼睛前面有雾似的一片,远处就看不清。一两个月后才渐渐好了。
刚过完元旦不久,所长就找胡风来了,手里拿了一份《人民日报》。我一看,就猜到是为了姚文元的文章来的。他问胡风读了没有,胡风说大略看了一下(其实他看得很仔细,上面划满了蓝铅笔的道道,我不得不将这份报纸藏了起来,怕他为此又闯祸)。
“那就写点感想吧!你知道,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你应该好好学习这篇文章。” 这一来,胡风可忍不住了:“姚文元的评论我不同意,尤其是把我和周扬拉在一起,说什么‘一丘之貉’。这不是事实。我和周扬在理论上有根本分歧,反周扬是我被判刑的罪名之一。他怎样评周扬我管不着,我没有资格写感想,我是犯人……”
※ 1968年:被判“无期徒刑”· 6年后相见 · 心因性精神病 ……
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一直拖延到1967年11月底。忽然来了一批人,宣布要他立即去成都。他当时很乐观,还暗中告诉我,一定是要解决问题了。但是,来人要我为他准备过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了情况并不是那么好的。胡风临行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也就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我知道,情况很不妙。但我记得他的话,要坚强,不要失望。我只能往好的方面去设想,盼着和他的重逢之日。
等呀,盼呀!1968年的元旦过了,春节也过了。管理所早就撤消了,这里只有我孤身一人。虽然是完全的自由,但生活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我却一点也没感觉害怕,因为我日夜都在盼着他的归来。
直到这年6月,茶场基建队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们首要的专政对象。从成都来了一批红卫兵,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他已被收监。红卫兵们抄了我们的家,封了我们住处的门,我被安排去医院劳动。一二年后,又让我去劳改二队劳动。直到 1973 年,将我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胡风那里。我们算是分别了五六年后,才在监狱里又得以重逢!
我们两人独自相对而站,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在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我实在找不出过去的他了。再加上那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真像哪个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和尚。
他对我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顺势跪在地上。这声音我是熟悉的,但是我止不住痛哭失声了。他却只呆呆地望着。这时,干事正走过来,他倏地站了起来。随着被干事叫走了。送他回来时,又命令他以后不准吓我。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我真不忍看下去。一个一辈子昂首挺胸活着的人怎么成了……
慢慢地,他才带着恐怖的样儿告诉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不是过去的胡风了,我是无期徒刑犯人,我是即将正法的犯人了,我是罪大恶极的……” 我几乎忍不住又要大声痛哭了,他赶紧捂着我嘴,“你不能哭。干事听到了,要加我的罪的。” 那惊慌失措害怕的样儿,使我明白他的脑子里已经混乱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了。
我只有克制住自己,慢慢将他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这一天,他帮我做家务,吃着我从成都带来的鸡蛋和腊肉。这些他五六年都没吃到了,他说连见都没见到,开始简直不敢吃,说会加罪的。我只好说:“这是我的,我要你吃的。有罪我来承担。”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 1970 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都是住的监狱,那情景可怕极了。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第二条罪名是“在主席画像上写反动诗词”。
他说:“我当然不会上诉。连判决书都没能给我看,话又听不太懂,这样能上诉吗?其实,我写的都是歌颂党的,他们却说我是恶毒攻击。这样青红皂白不分,我还说什么?不过,后来我明白了,罪名不止这些,而是将一切坏事恶事都怀疑上我了。他们判我无期不过是要在全世界找我的罪证,不定哪天就要枪毙我的。”
我来的时候,办公室干部曾和我谈过话,告诉我他有病,让我来照顾他,但他可不知道他得的是这种病,这病是应该送进医院去治疗的。
当天的深夜,他的病发作了。他突然要起床,说是有人要来带走他,还握手和我告别。我将他按下躺着,抱着他的头,像哄孩子似地抚摸着他的大脑门,又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我在这里,不用怕,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是的,我要用所有的柔情来温暖他那受惊的颤抖的心。
他总算安睡了,像过去一样安睡了。
我可睡不着了,直到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只见他一人坐在椅子上靠着他带来的铺盖卷。他见我醒来就说: “我可能就要走了,希望你别跟我去。那不知是什么地方,可能是水牢,刘文彩的那个,也可能是……”那么认真有把握,使我无法劝说他,只好说:“那就等着吧。我去做早饭。”这样,延续了好几天,后来,我说要给他拆洗被褥,这才将铺盖卷打开。
打开一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棉絮已成了破渔网似的大洞小洞,有的他用线缝过。我为他缝的红绸被面,那更是丝丝缕缕了。现在是用那张灰色的包袱皮和包铺盖的粗布做成的一床被子,多可怕的又破又脏的棉被啊!
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我看。我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过几天又再报上去,说实在不是自己干的,“我没干这事,不包了。”
但有一次他可神秘地告诉我:“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他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象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时好时坏,不能自拔。
我向干部提出应该给他一点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我的神经受不了。因此,就让我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我不愿白拿25元生活费,想缠麻鱼子一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公家。开始,这工作对他还有效,他一心缠麻理麻。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困难,也做不好。
他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我说,那就把我的给你吧,你的我再改改。
大热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总之,这种恐怖心理无法消除掉,生活虽然好了,但身体并没有好多少。他天天为大便不出来发愁,说是他吃这么多饭,不大便,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要他认罪,认他没有犯的罪。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我说这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终于晕倒了。
※ 死 去 活 来 ……
他在精神比较正常时,每天早晨都由他生火,那煤灶火我还弄不来,头天晚上我给他劈好柴,他选好炭,非常之认真,连几块大几块小都计算好。但有一天,我还没有起床,只听到他在院里说:“不好!怎么站不住?”
我感到真是“不好”了,赶快下床。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到外面一声“扑通”,等我出来时他已直挺挺地倒在台阶下了。我一看,他已失去了知觉,连瞳仁都散光了。我飞跑出去叫人,外面小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跑到外面巷子里叫,也没人应声。我再也不能远走了,只得匆匆地跑回来。走到门口时看见他的脚在动,我高兴地跳过去,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就想拉他起来。我用死劲想扶他回房,但实在力不从心,只好将他抱在怀里以免躺在地下受凉。
过了一会儿,他好多了,就说:“我怎么了!一阵头发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用力扶着我,我慢慢地挪脚,看能不能走。”居然,他在躺着由我拖着“走”了十来步。上台阶时,他用手爬,我用劲托,勉强进到了屋里,总算是活过来了!忽然,他哎哟一声大叫,“不好,裤子湿了。”还很抱歉地望着我,其实我是不会怪他的。这次,裤子里的大便特别多,我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他感到很轻松,好像是被解除了魔法。
等我将一切都弄好,准备做早饭时,才有一位干事进来。
一见到他,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经历了多么痛苦的一段时间。我说,他几乎不在人世了。
他们有点发慌了,很快就请来了一个女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极度贫血,原因是痔疮流血太多了。 决定给他打肝精针和 B12 。这些我在患贫血症时都打过,我就把这些情况向他解释。奇怪的是,他很听医生的话,说那女医生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负责尽职。他对她很有好感,天天等她来打针,劝他吃肉吃蛋他也不再害怕会挨斗了。后来我才悟到,这五六年来一直都是这医生给他看病,除我之外,就没有别人对他表示过关心。
他的身体日渐恢复,心情也稍趋正常。军管会主任来视察,对他说些应该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的话。对我可施加压力了:主要是责怪我没有好好帮助他。我无法申辩。你们专政机关帮助了十几年都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当然,我也希望他能有所“进步”,以至能出牢门!
我开始试着读报给他听,后来又学“老三篇”,一起读《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论》等。我还用问答形式记下了笔记,可惜,这简单的笔记被干事知道了要去看,就没再还我。
每天傍晚休息时,我们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我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了相当多。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我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这种安心学习,写材料而又自耕自食的生活在我们是多年以来没能享受到的,几乎忘了自己是住在高墙内被铁门关着没有自由的人了!
1975年春节前,照例狱中要开奖惩大会,胡风对此也能有所期待了。果然,监狱的书记来找他谈话了,这是他进大监以来从未有过的。书记说他有进步,至少将自称死囚的说法取消了,表示了他对政府对党的信任。胡风自己也承认是这样的。后来书记又说,党绝不愿把他关死在狱中,还是以宽大为怀,要释放他的。
我好久没见到他这般兴奋和高兴了。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者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对他还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燥地胡思乱想了。后来,他猜想可能是因为材料写得还不够全面,就又开始重新将所接触过的人来个全面交代。
“重评《水浒》”,“批林批孔”等给了他很不愉快的干扰,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小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我劝又劝不住,真是无可奈何。到后来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周总理的逝世对他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请罪,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几天后,他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他没什么事,我也没事。但他仍偷偷地写东西,写在小纸条上,还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我发现他是在写诗,不过写了他又撕了,看去情绪倒还正常。白天多半帮我种菜、浇水,有时也读书。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全集》,那是我争来的一套,我说是许先生送我的,所以就没当作胡风的财产充公。
※ 毛去世,出现喜人的转机
这几天过得很平安,没出什么事情。我常去城内书店租点书来看,有时也向他推荐,但他很少看,却对报纸发生了兴趣,《人民日报》是每天必看的。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两人站在屋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是深秋了,我们正坐在院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狄克何许人也?》的评论文章。我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这天正是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
傍晚,干事送报来时我们就问他,他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们。随后,北京就来人要胡风写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材料。当然没什么好写的,因为胡风同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来往,只知道一些传闻。另外,鲁迅先生这篇《三月的租界》是由胡风亲自送到《夜莺》杂志刊出的,他一直认为张春桥(狄克)一定是在报这个仇的。现在,他从写交代变为写揭发了,心情轻松多了。并且,北京来人对他的态度十分客气,这在他已是多年没有经受过的。
当年年底,送我们到成都附近的劳改医院为胡风治病。治得很好,他基本恢复了健康。三个月后,仍回到三监。我真担心,怕他又因失望而犯病。还好,他一心在写自己的思想收获,结果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了几十万字,并没再犯病。我们同三监的关系也不同了,干事常常来聊天,不过还是要他认罪,至少要认文艺思想方面的罪。——他没有照办,他们也无法说服他。小儿子在插队10年后考取了大学,他非常高兴,还写了诗给儿子。干事看不懂,可能扣下了没有寄出。
这期间他心中很高兴,对报上的大事十分关心,并且还常常吟诗祝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突然来通知说我们可以出狱搬到县委招待所去住。我们没去。几天后,监狱派人把我们护送到了成都,住进了省革委会的招待所。不久,小儿子也来到成都,和我们一起过了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
要胡风去省政协找秘书长要工作,这使胡风很生气:“关了我20多年,一出来就得去求人要工作。我已是70多岁的人,能干什么工作?不过是欺侮人罢了!”直到半年后,才通知他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 冬去春来,胡风得到应有的评价
1979 年6 月,四川省公安厅撤销对胡风无期徒刑的错误判决。
1980 年3月31日,中央组织部指示为胡风治病,把胡风与梅志接到北京,从此,胡风在此度过了安定的晚年。他一边治病,一边撰写整理回忆录。
9 月,中共中央重审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
 |
10 月,胡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后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胡风的8本文艺评论集,以《胡风评论集》为总题,分上、中、下三册出版。胡风在病中为该书写了长篇《后记》,追溯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总结了他一生的文艺观和历次论争的几个原则分歧的问题。他的回忆录陆续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但因长期遭受不幸,加上年迈,胡风终于在1985 年6 月8 日,因贲门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986 年元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悼词中称胡风为“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悼词最后指出:“胡风同志于1954 年7 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本站注:彻底、全面的平反则是在1988 年。)
【附 录】以下摘自《周正章:胡风追悼会的前前后后》——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6号文件,决定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
一、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理由:这是胡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应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一起考虑,如此指责不符合他的本意。
二、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理由: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对历史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
三、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理由: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李辉《文坛悲歌》第492页至第493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 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距1955年错立此案已有33年之久,离胡风逝世也有三个年头了!八年里三易结论,为平反史所罕见。
1955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胡风虽身处狱中,却从未缺席,一直作为陪绑者屡遭批判。于是,在中国当代政治斗争史上,一介文人胡风便成了一块不间断的政治较量公堂上的惊堂木。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第 1 页)
| 【延伸阅读】 |
||
| (本站 2005-07-12 编辑转发 / 2018-11-28 修订更新)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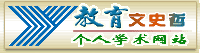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