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教育理论>应学俊:也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与王本陆教授商榷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教 育
历 史
时评杂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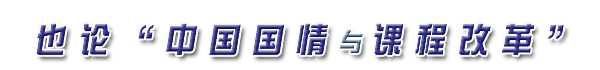 |
| —— 与王本陆教授商榷 |
| 安 徽 / 应学俊 |
| 撰稿:应学俊 来源:本站 原发表于《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1期 (本页浏览:人次)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提 纲】(可点击提纲选择浏览) (本文已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收录) |
邓小平先生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确实是非常英明睿智的。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九三年纲要》)在论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时,也明确将下列要求列入“原则”:“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⑸
但纵观《王文》,从头至尾却一句也没有提到“三个面向”之中的任何一个,通篇谈的是空空洞洞的所谓“国情”,而且断言“国情是决定课程改革的主要社会因素”。我们不知道《王文》再三强调之“国情”究竟包含了那些深奥的内容,竟如此讳莫如深?
三、也说“中国国情”与新一轮课程改革
《王文》如此重视国情,也对“国情”下了明确的定义:“所谓国情,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情况,是对主权国家内部情况和外部关系的总体概括。从其外延说,国情包括若干基本构成要素”——即“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力、文化心理、人口因素、国际关系”等。
但遗憾的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国情究竟如何?遍寻全文,终未觅得。如此空洞地谈论国情,我们不知道王本陆同志怎样运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怎样通过“实事”来“求是”?
笔者无意在此全面阐述中国国情,但对国情的某些方面还是有必要陈述一下,好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曾多次有过明确阐述。笔者谈点国情的具体情况——即使不够全面,也总比从提纲、概念到提纲、概念好,多少可以做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就与国家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国情而言,我国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这是不争的事实,及至2000年,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专科以上毕业生仅400人(即4%),高中毕业生13.8%……⑹ 在高等教育大力“扩招”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只有15%左右。教育投入不足,东部和西部、城乡、沿海地区和内地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国情就无需细说了。
而就“基础教育的基本国情”而言,早在1985年,中央在肯定解放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指出:“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⑺这难道不正是“国情”吗?1999年,中央针对基础教育现状的弊端指出:“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要“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⑻这难道不也是国情和中央的要求?王本陆先生为何不提这些“国情”?
就我国基础教育学校的智育而言,早在7年前,《九三年纲要》就有针对性地指出:“……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毫无疑问,中央的决定是基于“国情”做出的,否则岂非无的放矢?而所提的这些改革要求和方向,难道不正与“建构主义理论”核心有所吻合?
但是,《王文》在上述这些方面似乎是视而不见的,甚至是否定的——《王文》这样表述:“立足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历史进程来观察,立足于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发展史来认识,那就会发现,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虽然有不少弊病,但其基本性质不是传统教育或应试教育,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这便是王本陆先生对中国“教育国情”的判断和基本评估。按王本陆先生所论,中央以及全国的众多教育学者、一线教师以及更多群众,对中国教育的感受和批判都是错误的、多余的,“应试教育”也是不存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作出的有关教育改革的决定和阐述也都是“杞人忧天”了,教育无须改革,对某些弊端有所克服、改进就可以了——因为中国教育本质上已经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了。呜呼,王本陆先生如此研判!
《王文》还再次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方法把国人对教育主要弊端的针砭加以极端化的“归谬”:“一些论者一提到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就以为还是凯洛夫那一套,所有学校都搞应试教育,课堂教学都是一灌到底,学生都是高分低能,……”殊不知,只要把《王文》中的“所有”、“都搞”、“都是”实事求是地换成“基本是”、“大多是”等,那真的就是对中国基础教育、教学方法状况很好的概括。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笔者在拙文《“应试教育论”可以休矣——与王策三教授商榷》⑽中有过专门阐述,在此不想赘述了。
诚然,《王文》也不得不笼统承认我国现行基础教育有不少“弊病”,但究竟有哪些弊病,《王文》却不能或者说不敢如中央决定中那样具体地加以阐述,只是轻描淡写笼统而论。大约《王文》认为那不是主流,是非本质的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这是“主流“——可非常遗憾的是,中央就是针对如此“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多次研究,多次作出改革的重大决定;甚至连总书记也为此发表专题的讲话。不是面对国情,那中共中央国务院乃至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岂不是都在无的放矢?不知王本陆同志究竟以怎样的思维逻辑理解这些现象的前因后果?
其实,谁也不会否认我国解放后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开得最灿烂的花朵里面也会隐藏着致命的害虫或病毒;果树上从无到有长出了硕大的果实,这是发展,是成果,但往往在鲜红欲滴之硕大的果子里,害虫或病毒正在疯狂地吞噬着果子的内核和果肉,而且疯狂地繁殖着自身——导致果实的“异化”——这还用论证吗?教育与执政党的发展其性质并无本质不同——没有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改革,就无法“保鲜”,就会“异化”。我们能否认中国教育正在加快着“异化”的进程吗?教育的本质属性现在还有多少堪称“保鲜”?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和显而易见的道理,国务院2001年再次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论及课程改革时,《决定》明确指出:“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继续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并关注情感、态度的培养;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 ⑾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还需要论证吗?《决定》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制定的依据,正是我国的综合国情和基础教育国情以及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之国情。而新一轮课改的理论以及借鉴的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无一不是对应这上述教育改革的要求亦即中国基础教育的弊端——尽管新课改包括理论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仍须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但我们岂能说新课改是脱离了“中国国情”的?如何扯得上“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国情”?
(未完,点击这里:紧接下页)
| 【延伸阅读】 |
||
|
||
| (本站 2007-02 编辑发布 / 2019-02-28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