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陋室文化>应天常教授专栏>走出他的身影,是时候了——纪念张颂先生逝世六周年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应天常教授专栏相关文章:
本站评论(更新):
重读历史(更新):
走出他的身影,是时候了—— 纪念张颂先生逝世六周年 |
| · 应天常 · |
| (本站声明:应天常教授授权在他此个人专栏首发。任何媒体 若欲转载,须征得应天常教授或本站允许,否则视为侵权。) |
| 撰稿:应天常 信息源:作者赐稿 本站编辑首发:2019-01-21 (浏览数: 人次) |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回忆与张颂先生二十余年亦师亦友的情谊,赞扬其学术人品和敬业精神,肯定其理论贡献,遵循先生“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的教诲,作者从语言学、语用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评述张颂先生播音主持理论的局限性,强调重新建构播音主持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 键 词】 张颂先生 播音主持 学科理论体系 |
(点击这里:承上页)
最近读到赵琳博士《半个世纪的开拓》一文,颇有些感慨。
她说:
“今天中国传媒界高等学府里,三代教师都是张颂带出来的。培养了包括李瑞英、罗京、康辉、张政、王雪纯、周涛、鲁健等在内的全国3万多名代表国家形象的播音员主持人,培养了300多所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和数以万计来自海内外的语言工作者和高校专业教师,有人说他‘一本书养活了一支队伍’,先生却幽默地说: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②
“一本书养活了一支队伍”,这是张颂先生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可能潜伏危机;先生“一本书”带出了“三代教师”,包括“300多所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师”、3万多名代表国家形象的播音员主持人,还包括一群博士,我想,“七十二贤人弟子三千”的孔子望尘莫及了,不过,赵女士此文是贺寿之作,是不是包含溢美的夸饰,不得而知;但这也难免“近亲繁殖”的弊端——赵琳在文章中坦言:“有年轻教师感叹:‘我们要写的,他老人家早已写过了。’”
播音主持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理论库存贫乏,需要积极探索、博采众长,有一个积累完善的过程。如果“一支队伍”围着“一本书”转,必然导致学科理论探索的懈怠、导致对权威的盲从、导致学科理论体系的固化和板结,也导致人才培养和媒介需求的脱节。这么多年,理论的机械复制、实践的模式挪用,审美情趣单向度的塑造,年复一年循环,成为习以为常的现实。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睿智的学者,张颂先生是有警惕的。他懂得,在学术领域不存在不可撼动一家之言、一定之尊,学科建设需要更多人的参与,理论研究是“永远在路上”的事情。对此,赵琳在文章中透露:
张颂先生曾经说:“我们的播音学完成了,我们没有话说了——不客气的说,这都是懒汉和懦夫的思想!”
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③
“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说得好极了——如果不是看到赵琳博士的文章,我很难知道张颂先生曾如此地渴望批评。张先生是对的,亚里斯多德说“学术始于质疑”,任何一门新的学科理论,都是在批评和探究中成长成熟起来的——但是,很奇怪,先生倡导的学术批评没有正常开展起来。
其实,不是没有批评,批评是有的,就是针对张颂先生的。现在甚至可以说,如果当年先生有面对批评的严谨,他的《中国播音学》会是另一个样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倡解放思想,广播电视界的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张颂著《中国播音学》尚未问世,对其相关理论观点的质疑就“暗流涌动”了。
——这是张颂先生始料未及的事情。先生强烈的学术自信让他忽略他与一些人在语言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深刻分歧。后来,我们看到十分有趣的现象:一面倡导批评,一面抵制批评,先生和他的一些弟子打了一场“播音学保卫战”。
如今,我们回溯经年已久的这场论战,并非“闲笔”,花一点笔墨不仅有助于厘清几个搁置已久的学术论题,推动学科理论的建设,而且,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理论探讨和媒介批评,也是有价值的,不妨展开来说。
四、“批评”在语言的“魔圈”里
这场论争,肇始于张颂先生将主持人语言“纳入”《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的思路——1991年,先生的弟子王旭东在《现代传播》杂志第1期发表《“播音员涵盖主持人”论略》,全面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主持人只是播音这棵大树长出的一个分支,人为夸大二者的区别,让主持人独树一枝,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王旭东直而言之:“节目主持人只是播音员的一种法定身份,主持人语言只是播音员的一种特定方式……”
由此,播音员是不是“涵盖”主持人,引起了学界的一场争论。
无论怎么说,这并不是一个艰涩抽象的学术命题,因为从媒介职能的区别、从角色地位的划分、尤其从语用方式的迥然相异等方面看,主持人与播音员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如今,却成了越说越糊涂的话题。
我也觉得困惑不解,想起了霍姆巴尔特(Htlm boldt)所言:“人类用自己的存在织成语言之网,然而又陷入这一张大网。每一种语言都围绕着使用它的人划定了一个魔圈。”④ 后来知道,我这个有趣的联想是有共鸣的,那就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李东先生,他堪称最早尝试走出“魔圈”的人。
我后来到广州工作,同这位引领潮流开创“珠江模式”的广播人相识。
李东先生通过自身的实践体验发现播音员和主持人话语方式的差异性,经过思索和论证,于1993年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了《走出“魔圈”——与张颂教授商榷兼论主持人语言特征》的论文,对“播音员涵盖主持人”的观点提出学理性质疑。此文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学会“金笔奖”。
张颂先生随即为此出版《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对李东先生的观点进行批驳,愤激溢于言表。他指出:
“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传播媒体加入媚悦‘上帝’的行列……语言发生了危机,危机产生了恶果。”他希望“引起一场论战,以便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⑤
先生渴望“论战”,很快就有了回应。
全国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副会长白谦诚先生撰文论证“主持人替代播音员”的必然性,从根基上撼动了“播音本位论”;但是“取代论”并未使“涵盖论”的讨论转向,大概“一支队伍”“三代教师”的能量是巨大的,20年来出现了许多阐述“涵盖论”的文章,而质疑商榷的声音比较微弱。由于没有共同的话语平台,大多“论”而不“争”,一篇篇“独白”只是隐晦曲折的文字较量罢了。
我是1996年介入这场争论的。当时徐立军先生在《现代传播》发文提出了“主持式播音”的概念,我深感喻证式思维走不出既定的理论框架,于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拙著《节目主持语用学》中进行比较深入的批驳。⑥
但是,这些持论有些犀利的质疑,换来的是“鸟鸣山更幽”的寂寞。
后来,先生为了深化他的观点,强调“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并指出播音是一种创作,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谈话,所以不能称之为“有稿说话”、“无稿交谈”。从此,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和主持的一些教材中,高频率使用所谓“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这两个概念,“做实”了主持人用“说”在“播音”的合理存在,这样,“播音”就名正言顺地“涵盖主持”了。
但是“泰斗”的权威没能完全遏止学界质疑的声音。面对撼动“涵盖论”论述日渐增多,先生难掩内心的愤懑。于2001年在为研究生的著述作序时,顺带对“涵盖论”的质疑再次作出回应。先生一改文风,不无嘲讽地说:
“……连这些最基础的知识都不了解,仅凭主观的臆断,那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呢?康德说,他不怕别人驳斥,倒是很怕被人误解。我们知道的有些‘理论’针对‘中国播音学’说的许多话,已经不大像是‘误解’了,倒有点儿‘曲解’的味道了。那些热衷于此的同志,正在向假想敌开战,很有点像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⑦
张颂先生是中国播音学的开创者,学术地位有目共睹。但是,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回应质疑,探究就很难深入了。既然说“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怎么讨论播音与主持的区别就是将《中国播音学》当作“假想敌”?先生也许把质疑者也当作“假想敌”了吧?看来,在“魔圈”里很难走出来了。
直到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部主任张君昌先生撰文指出:
“播音界不应该操着‘涵盖’的老观点不放……主持人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占据大半江山的今天,仍然把它当作播音的一个小小的‘分支’看待,不利于事业的发展。”⑧
这似乎不能算是争论的结论,因为对先生权威性论断没有丝毫“撼动”。
五、“批评”成为永无终结的悬疑
无序的论争一时难以止息,有些质疑甚至直接来自这所大学的学生。
我看到两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生在《中国广播》杂志联名发表《“学院派”播音主持问题出在何处》的文章。他们指出:
“我们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是失败的。传统播音主持教学不适应现代传播的急剧变化……主流播音与现代口才训练脱节,教育者故步自封和学生实践中的自我定位发生误差。”⑨
另一位播音系毕业生说:
“有些理论是显得有些乏味的条条框框。汉语有声语言创作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我认为,我所学习和实践的汉语有声语言创作是一种传统的甚至有些过时的风格。新时期的广播电视需要多样化的有声语言表达样式。我惊异地发现,实践中那些我曾认为把我框住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似乎消失了,初出茅庐的固定腔调没有了,话筒前的状态越来越自如。”⑩
还有人指出:
“被规训的播音学和播音学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亟需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重新定位。”⑪
“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不能适应工作,出现了人才供需的失衡,怎样培养出既具有高质量理论基础又能适应播音与主持领域各项工作的优秀人才,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⑫
……
我不知道先生生前是否注意到这些议论。
现在的问题是,近十多年“播音主持”专业“野蛮生长”,据赵琳博士说,全国开设这个专业的有300多所高校(不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大批毕业后多数“分流”出去,只有极少数“拔尖生”进入媒体,公允地说,他们的质疑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实践检验的反馈,值得重视。
当我想到,直至现在,一批接一批的学生还在“一本书”这个理论体系和训练模式里面“转”,用现在的网语说,有点细思恐极。
情况本不该如此——无论怎么说,先生的理论体系早该改弦易辙了。今天想起这场争论,我仍觉得沮丧。我不怀疑先生倡导学术批评的真诚,但是它一开始就走入了岔道,至今留下一片茫然。
显然,先生在论争的初始阶段对李东的“反击”用力过度,产生了某种震慑的力量,打破了交流探讨的平衡,而弟子“助攻”形成的话语倾向更使探讨难以深入。坦率的说,我与先生的交往可谓过从甚密,却怯于在理论话题上“摊牌”;我宁愿在著述的表述中与之针锋相对,却出于敬畏之心,不忍当面冲撞先生不可撼动的尊严——我想,以先生的睿智和博学,我有理由期待先生自我修正。
我甚至隐然觉得,先生有生之年,对于这个“跨世纪”分歧应有所回应。于是,在那个夜晚去了一个电话,请他对我即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撰写序言,附带对我进行一次“学术清算”。先生沉吟片刻,答应了。
看了我的书稿,他很快发来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这篇写于2009年末的文字,重述了他的某些观点,其中,也包含先生对我的“终结评价”。
他说:
“我同应天常教授相交甚早,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见面,相谈甚欢,十分融洽。我对他是很敬佩的,因为他为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出版过数本专著,在这个领域研究相当深入,学术水平很高。他数十年的执着追求和埋头写作,成果丰硕,受到了业界的推崇和尊重。他的著述成为我们学科理论宝库的一个亮点,是同他的学术视野宽阔、理论造诣深厚分不开的。他的学术品格、学术态度,是摒弃了当下的浮躁和低俗,蔑视着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和利欲熏心之辈的。”
在先生面前,我有自知之明。尽管先生对我的肯定弥足珍贵,我却只能看作宽厚长者的鼓励和鞭策,因为它没有显示先生的理论观点有丝毫的松动或改变,当然,先生也没有回避我们之间的分歧,他说:
“当然,毋庸讳言,我们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在学术观点上‘各抒己见’又‘畅所欲言’,恰恰说明学术氛围的宽松活跃,学术自由的平等愉悦,学术态度的认真负责,学术作风的率真质朴,‘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恰是境界高远的表现。任何学术认识,都可以在探索中不断深化,这是规律。观点的分歧,可以在多次讨论中、在各抒己见时求同存异,这是进步。让我们都参加这种研讨,丰富理论宝库,促使我们的理论日臻完善。而在这个方面,应天常教授的论述功不可没。”⑬
我忖度先生珍惜情谊,以宽阔的胸襟对我的研究予以肯定,但不愿正面触及敏感的论题,或者说,先生不愿我们进入那个“魔圈”走不出来。
不过,我仍难掩莫名的惆怅——我们初次相识就为“口语”概念的界定开始争论,20年来在学科理论研究中观点相左,却始终论而不争,谈笑风生,可谓友情甚笃。但是,我的“畅所欲言”换来了“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留下永无终结的悬疑——呜呼!只能如此了,我将永存那带有温度的记忆。
“墓草萋萋,落照黄昏,音容犹在,斯人邈矣。”
六、先生的语言观与时代脱节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我没有因为观点分歧改变对张颂先生的人格评价。在我眼里,先生是富有个性的人,正直高尚不一定完美无缺,片面的深刻呈现多元,何况美好往往呈现残缺,我们有时面对某种偏执,如同面对断臂维纳斯——不是曲意“溢美”,无论如何,在与先生的多年接触中,我觉出一种令我敬重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告诉我,虽然先生驾鹤远行,对我如今撰文近乎“数落”的诘问和质疑,仍会一如他生前,有一种令我感动的豁达和包容。
先生的教诲“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言犹在耳,如今,为了这门学科不是走向衰落,而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认为,有必要将播音理论批评和探讨继续进行下去。在这里,不揣浅陋,我想以那一场“涵盖论”之争为蓝本,谈一谈张颂先生播音理论方面的某些局限性。
(未完,接下页)
【相关链接】
( 2019-12-22 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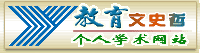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